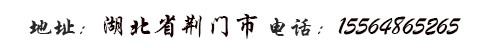花季的托斯卡纳
|
#Julian书友会# 周末读书会 好书分享—— 《劳伦斯散文选》节选 《花季托斯卡纳》 花季托斯卡纳 每个国家都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大放异彩的花。在英国,是雏菊、金凤花、山楂和立金花。在美国,是秋麒麟草、星花草、六月菊、八角莲和我们称之为紫苑的翠菊。在印度,是木槿、曼陀罗和金香木。在澳大利亚,是金合欢和奇形怪状的尖叶石楠花。在墨西哥,是仙人花,人们称之为沙漠玫瑰,在刺丛中开得可爱,开得晶莹剔透;还有长长的丝兰花,开着奶黄色铃铛样的花朵,像是垂落的泡沫。 但在现今的地中海,如同出现阿格西大商船的十六世纪(我们希望永远如此),这样的花是水仙、银莲花、日光兰和长春花。水仙、银莲花、日光兰、藏红花、长春花和欧芹,单单被地中海人赋予了独到的意义。在意大利也有雏菊,三月的帕斯腾,雏菊盛开,像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白地毯;托斯卡纳则遍地开满了地黄连。可是,再怎么说,雏菊和地黄连也是英国的花儿,它们只对我们和北方人才具有妙意。地中海地区有水仙、银莲花、长春花、日光兰和葡萄风信子。这些花儿,只有地中海一带的人才能听懂它们的话。托斯卡纳这地方花儿开得奇盛,因为这里的气候比西西里潮湿,比罗马一带的山区更适合作物生长。托斯卡纳勉强能够远离尘嚣,自得其乐。这里有多座山头兀立,但各自相安无事。这里有众多小小的沟壑,峡谷中的溪水似乎各行其道,全然不在乎什么大江大海。这里布满了千千万万道全然与世隔绝的小小沟坎儿,尽管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一直有人耕作。人类生生不息地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种植葡萄、橄榄和小麦,他们忙碌的双手和冬播的脚步以及目光温顺、步态悠缓的耕牛并未将这里的乡村毁掉,并未让土地裸露、光秃,并未将潘神和他的儿女们从土地上驱走。溪水在隐秘的野石上汩汩流淌,在黑刺李丛中淙淙低吟,和着夜莺的歌唱,舒缓而坦荡。 不可思议的是,托斯卡纳这样经过彻底开垦的地方,每五英亩土地上的一半物产要养活十个人,可还是有如此大的地盘生长鲜花,供夜莺藏匿。只要有突兀的小山包,一座座山头各成一体,人就要建起自己的花园和葡萄园,雕塑他自己的风景。说起古巴比伦的金字塔形庙宇里曾建有梯地花园,整个意大利,除去平原地带,就是一座梯地花园。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一直耐心地修整地中海一带的乡村,将小山包修圆,将大大小小的斜坡次第修整成天衣无缝的梯田。成千上万平方英亩的意大利土地在人的手中堆砌而起,修整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平地,再为此砌起石墙保护之,这些石头就采自这刨开的土地。这是无数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它精雕细琢出了这里全部的风景。这种别样的意大利美景精致而自然,因为人在敏感地摸索着让土地丰产时既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又不至于伤害土地。 这说明,人可以居于土地,依赖土地,但不破坏土地。这一点在这里做到了,在这些雕塑过的山上和精雕细琢了舒缓梯田的斜坡上。 当然,你不能在四码宽的梯田上驾驶蒸汽犁。这些梯田随着山上的坡度和开垦的界线而缩进、拓宽、下沉和上升。这些小小的梯田上要种玉米,现在则若隐若现地长起了灰色的橄榄,蜿蜒起了葡萄藤。如果牛能迈着可爱的步伐一步一顿前行,它们就能犁耕这狭窄的田地了。可是地边上得留下一道窄窄的边儿,让它长草,为的是护住下方的石墙。如果这梯田太窄,无法用犁耕它,农夫就用锄头刨,他们也得留出一条窄窄的草边儿来,这有助于下雨时保住梯田不被冲垮。 就在这里,花儿得以藏身。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这片土地被翻耕,两年一次,有时三年一次,几千年下来,一直如此。可是花儿从未被驱赶出去。 曾有过强有力的挖掘和筛滤,地里挖出的小小球茎和根茎都扔了,毁灭了,寸草不剩。 可是,春回大地,在梯田的边沿儿上,在梯田的石头角落中,蹿出了乌头、藏红花、水仙和日光兰,还有生生不息的野郁金香。它们生长于斯,悬挂在那里,在生死攸关的边缘,但总能顺利成活,从不失去自己的落脚点。在英国,在美国,花儿被连根拔起、赶走,花儿变成了逃犯。但是在这精雕细琢的古老意大利梯田上,花儿在舞蹈,在挺立着。 春天是在第一朵水仙的伴随下到来的,这茬儿水仙开得冷,开得羞赧,还带着些儿冬天的寒意。这一小簇一小簇奶黄色水仙,黄色的杯口形花萼看似花儿上的蛋黄。当地人称之为tazzette,意为小杯子。这种花生长在草木茂盛的梯田边沿上,稀稀拉拉的,荆棘丛中也有它们的身影。 在我看来它们是冬季的花儿,散发着冬天的气息。春天是在二月份冬乌头开花时开始的。二月初某个冰冷的冬日,当积雪的山上寒风袭来时,你会发现橄榄树下的休耕地上,紧贴着地面拱出了淡黄色的小花骨朵儿,紧如坚果,长在紧贴地皮的绿色圆花托上。这就是冬乌头花,出其不意地绽放了。 冬乌头花是最为艳丽的一种花儿了。像所有早春绽放的花儿一样,小花朵初放时很是无遮无拦的,不像雏菊或蒲公英那样外面包着一层绿色的萼片。那娇弱的黄花朵衬在圆圆的绿花托上,迎着风雪绽放。 风要摧毁它,但无法得逞。北风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二月天。那紧紧抱成一团的冬乌头花骨朵儿膨胀开来,变成了轻轻的气泡,像绿色托盘上的小气球一般。阳光灿烂,令这二月天一片明媚。到了正午,橄榄树下的一切都成了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小太阳,冬乌头开得魅力四射,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美妙的甜丝丝的味道,像蜜,而不是水仙的冷香。一只只棕色的小蜜蜂在二月天里嗡嗡叫起来。 直到午后,夕阳斜下,空气中又弥漫起雪的气息来。 可是,到了晚上,在桌上的灯光照耀下,乌头花又散发出浓烈的芬芳,春天的醇香令人几乎要愉快地哼唱,恨不能成为一只蜜蜂。 乌头花期并不长。可它们在各种奇奇怪怪的地方绽放—在挖出的泥块上,在蚕豆茁壮成长的地方,在梯田的边沿儿上。不过它们最喜欢的还是休耕一冬的土地。在这样的休耕地上,它们欣欣向荣,炫耀表现出自己迅速抓住机遇生存的能力。 两周之后,在二月结束之前,乌头那黄色的泡泡花儿就化作春泥了。不过,在某个舒适的角落里,紫罗兰已经开得黑紫一片,空气中已经弥漫起另一种清香。 菟葵像冬季遗留下的碎片,在所有荒蛮的地方绽放。金盏花在炫耀着最后一茬明晃晃的红莓子。菟葵是冬玫瑰的一种,但是在托斯卡纳,它从来也不开白花。菟葵在十二月底时在草丛中崭露头角,冬季开花,叶子呈浅绿,形状可人,生着淡黄的雄蕊。这种花像所有冬季花一样色泽晦暗,在枯草中鹤立,枝叶浅绿,挺立着,像小小的照不出什么的掌中镜。最初,它们在花梗上独自绽放,娇小可爱,透着冷艳,显出一副不愿让人触摸、不引人注目的样子。对这样的花,人们本能地敬而远之。可是,随着一月结束,二月来临,菟葵这等葱茏的冬玫瑰变得跃跃欲试起来。它们的嫩绿开始发黄了,呈现出淡淡的草绿色。它们长起来了,一丛丛,一簇簇,组成形状各异的绿色灌木丛,花儿开了,开得招摇,花朵垂首,但依旧招摇,那是菟葵的招摇方式。在有些地方,它们在灌木丛中,在溪流上方聚成一团一簇,从中走过,会发现它们的花瓣儿闪着微光,这一点很像报春花。是很像报春花,但菟葵的叶子生得粗糙,形态骄横,像冬天里的蛇。 从花丛中走过,你会把金盏花上的最后一些猩红莓子蹭落。这种矮小的灌木是托斯卡纳的圣诞冬青树,只有一码左右高,在又尖又硬的叶子中间长着一颗鲜红的莓子。二月里,最后一颗红果滚下多刺的羽叶来,冬天也随之而去了。潮湿的土地上早已生出紫罗兰来。 不过,在紫罗兰绽放之前,藏红花已经开了。如果你穿过高高的松林向山上走,直到山顶,你可以朝南看,一直朝南看,你会看到亚平宁半岛上的皑皑白雪。如果是在一个碧空万里的午后,能看到远方的七层蓝山叠嶂。 然后,你在那朝南的山坡上坐下,那里没有风,无论一月还是二月,不管刮不刮北风,这里都很温暖。这片坡地让太阳烘烤得太久,一遍又一遍地烘烤过;让一场又一场雨浸润过,但潮湿的时间从不过长,因为它是石山,整个面朝南,十分陡峭。 二月天里,就在那为阳光烤炙的荒蛮乱石坡地上,你会发现第一茬藏红花。在那全然荒芜的乱石堆上,你会看到一颗奇特闪烁的小星星,很尖但很小。这花儿开得平坦,看上去像小苍兰,奶油色,上面的黄点儿似一滴蛋黄。没有梗儿,像是刚刚掉落在这炽热的乱石堆上的。这是第一茬山藏红花。 在阿尔卑斯山北麓,漫长的冬天不时被挣扎几下便溃退的夏日所打扰;而在南麓,漫长的夏天则时而被可恶的冬天所打扰,这种冬天从来也站不稳脚跟,可就是下作而顽固。在阿尔卑斯山北麓,你尽可以在六月里遇上一个纯粹的冬日。在南麓,你竟然可以在十二月、一月甚至二月里遇上一个仲夏日。这两种情形的出现没有定准,但是,朝阳的一面永远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而北麓则总是一片灰暗。 可是作物,特别是花,在阿尔卑斯山两面,南面的花并不比北面的花开得多早。整个冬季,花园里都开着玫瑰,可爱的奶黄色玫瑰姿态优美地斜挂在枝上,显得比夏日里更加纯洁而又神秘。到一月底,花园中的水仙就开了,接踵而来的是二月初的小风信子。 而在田野里,花儿并不比英国开得早。到二月中旬,紫罗兰、藏红花和报春花才见初绽。而在英国,二月中旬的时候,篱笆灌木中和花园的角落里也能发现三两朵紫罗兰和藏红花了。 托斯卡纳的情形毕竟还是不同些。这里有好几种野生藏红花:有尖长紫红的,有尖长奶黄色的,生长在无草的松林间山坡上。但漂亮的花都生长在树林一角的一块草坪上,在陡峭、松林蔽日的山坡下隐藏着那块低洼的草坪,整个冬天草丛中都渗着水,茂密的灌木丛中溪水在流淌,夜莺在此引吭,五月里唱得最欢,那里的野百里香透着玫瑰色,夏日里招来满头满脑的蜜蜂。 淡紫色的藏红花在这里最为怡然自得。紫色的花儿从洼地中深深的草丛里探出头来,像是有无数朵花儿在此安营扎寨。你可以在黄昏时分看到它们,那阴暗的草丛世界静得神秘,草丛中所有的花蕾都紧闭着,闪烁着微暗的光芒,恰似打了千层褶的帐篷。北美印第安草莽们都是这样,在西部的大山谷中安营扎寨,夜间合上他们的帐篷。 可到了早上情形就不同了。强烈的阳光辉映着绿云样的松树,晴空一片,充满生机;流水湍急,依旧被最后一些橄榄汁染成了棕色。那一盆地的藏红花开得让人瞠目。你无法相信这些花朵的确娴静。它们开得如此欢畅,它们橘红色的雄蕊如此蓬勃,铺天盖地,如此妙不可言,这一切都昭示着灿烂的狂喜,涌动着的鲜亮紫色和橘红,以某种隐蔽的旋律,奏出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你无法相信,它们纹丝不动,仍能发出某种清越的欢乐之音。如果你沉静地坐着凝视,你会开始同它们一起活动起来,如同与星星一起运动一样,于是你能感觉到它们辐射的声响。这些花儿的所有小小细胞一定随着生命的绽放和呢喃跃动着。 棕色的小蜜蜂从一朵花儿跳到另一朵花儿上,俯冲、试探,然后飞走。大多数花儿都已经让它们劫掠过了,偶尔还是有一只蜜蜂头朝下在花心里扑腾一会儿,还是能从中找到点儿什么。所有的蜜蜂都长着小小的花粉囊,那是蜜蜂的面包袋儿,就长在它们的臂肘窝里。 藏红花能美丽地开上一周多点儿,待它们开始偃旗息鼓,紫罗兰便茂盛了起来。这时已经是三月了。紫罗兰像黑色的小猎狗一样探头探脑好几周,然后蜂拥而出,在草丛中,在丛生的野百里香中,直到空气中都弥漫起淡淡的紫罗兰香味来。而曾经为藏红花所盘亘的边沿现在则缤纷一片,开满了紫罗兰。这是早春的甜紫罗兰,开得野,开得恣肆,阳光下的山坡上满眼的紫色烟花,偶尔还会有一朵晚开的藏 红花依旧挺拔,摇曳其中。 此时已是三月,花儿来得急。在另一条朝阳流去的溪流旁,荆棘丛和悬钩子丛中,整个冬天里藏红花都开得素雅得体,可这时却突然绽放出朵朵雪白的报春花来。荆棘丛中,水边上,一簇簇、一束束报春花怒放着。可是同英国的报春花比,这里的花儿显得素净、苍白、单薄些。它们缺少欧洲北方的花那丰满的神韵。人们容易忽视它们,而把目光转向岸上耸起的神情严肃的高大的紫色紫罗兰,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座神奇的小塔般的葡萄风信子。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花在初绽时能比蓝色的葡萄风信子更加迷人。可是,因为它花期太久(至少有两个月之久吧),而且不停地怒放,人们往往忽视它,甚至有点小瞧它。这可是太失公允了。 葡萄风信子初绽时呈蓝色,开得茂盛蓬勃,在没有返青的草地上显得很有韵味。顶上的花蕾是纯蓝色的,包得很紧,浑圆的纯蓝色花蕾,完美的暖色蓝,蓝,就是蓝。而下方的铃铛花儿则是深紫色的蓝,开口处涂着一抹儿白。但是这些铃铛花儿现在还没有一朵凋敝的,它们不肯离开那些稀稀拉拉的小青果,这些果实以后会毁了这葡萄风信子,教它看上去赤裸裸的,显得过于实用了。所有的风信子打籽儿时都是这副样子。 但是,最初你只看到一团深蓝色的花冠,到黎明时分绽放,美得出奇。如果我们是一些娇小的仙女儿,而且只活一个夏天,在我们眼中,这些花铃铛该是多么美丽,这些从夜晚到黎明都呈蓝色的花球。它们 在我们头顶上长得茂盛、饱满,那些紫色的花球会摧开那些蓝色的花球,冒出星星点点的白乳头,让我们觉得有一个神在里面藏身。 事实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些是多乳的月亮和狩猎女神之花。不错,伊费瑟斯的大母神生着一簇簇乳房,恰似胸脯上盛开着一朵朵葡萄风信子一般。 到三月的这个时候,小溪旁的树篱丛中,黑刺李开花了,白花如烟,坡地上桃花独自绽放粉色。粉红的杏花儿已经变浅,渐渐凋谢。但桃花却颜色重,一点儿也没有去意,这说明它像肉体,而树则像一个个孤独的人,桃树和杏树均如此。 这个春天里,有个人说:“哦,我对桃花一点儿也不在意!它粉得俗气!”不知道粉红色何以“俗”。我认为粉红的绒布有点儿俗气,但可能那是绒布的问题,怨不得粉红色。而桃花的粉红是一种美丽的肉感粉红,离俗气有十万八千里呢,粉得奇,粉得雅。在风景中,粉红显得特别美,粉红的房子,粉红的杏花,粉红的桃花儿,红中透紫的粉红李子,还有粉红的日光兰。 在春天的绿色中,粉红色是那么抢眼,那么独特,这是因为告别冬季时初绽的花儿总是白的、黄的或紫的。此时,地黄连花期已过,沿着地边儿长出了高大结实的黑紫色银莲花,花蕊是黑的。 这些巨大的黑紫色银莲花真叫奇特。在某个阴天里,或者是晚上或早晨,你可能从它们身边路过但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可如果是在晴好的天气里你路过它们身边,它们似乎是在扯着嗓门儿向你吼叫着,似乎要将其深紫色吼得漫天都是。这是因为它们吸足了阳光,热了,盛开了。可是,它们花蕾紧闭时,则如绸缎般光洁,头弯曲着如同雨伞把儿,外表苍白无华,毫不引人注目。它们也许就在你的脚下,可你不见得注意它们。 总之,银莲花是怪花。离平原最近的山上,只有这种巨大的黑紫色银莲,这儿一簇,那儿一簇,但不多见。但两座山开外,则生长着一种紫青色的,与绿色的麦苗相辉映。它们虽然仍属于宽叶儿黑蕊的那一种,但比我们这边黑紫色的花要娇小得多,颜色浅得多,更像绸缎。我们这边的花是一些皮实厚实的蔬菜似的花,可又不很茂盛。那边的花则娇小光洁可爱,整片地里的麦苗与之同绿。而一旦天气暖起来,它们还会散发出十分甘美的气息来。 在牧师的领地上,生长着一种猩红的银莲花,俗称“阿童尼斯之血”:只在一个地方,在一道梯田边沿下长长的一条小径旁。这种花,你不在阳光下寻找,就永远也看不到。花蕾紧闭时,它们绸缎般银色的外表让自己难以引人注目。 可是,如果你在阳光下走过,会突然看到有一些猩红色的小花仰面朝天,那是世上最可爱的猩红色景象了。“阿童尼斯之血”,其内表皮如同天鹅绒一样细腻,但又不像天鹅绒玫瑰花上的那种绒面。是从这内在的平滑中发散出了红色,那么纯正,不知尘世为何物,一点儿也没有泥土气,可又很是结实,并不透明。一种颜色何以具有如此强的抵御能力保持自身的纯正?它看似聚集着光芒,可毫不璀璨,至少一点儿都不透明,这真是个问题了。罂粟花鲜艳时呈半透明,郁金香的纯红像晦暗的泥土。但是“阿童尼斯之血”则既不透明也不晦暗。它仅仅呈现出纯粹的浓烈的红色,像天鹅绒而无绒,猩红,但没有光芒。 这种红色在我看来是夏季到来的完美预示,就像苹果花上的红色及其以后苹果本身的红色,这些红色告诉人们夏天和秋天快到了。 现在红花开了。野郁金香正含苞欲放,灰色的叶子像旗子一样垂落着。一有机会,它们就会群起齐放。不过到三月底或四月初它们就谢了春红。 天气仍然在转暖。高高的水渠旁,常见的洋红色银莲花或垂落着银色的穗子,或冲着太阳绽开其巨大的雏菊形洋红色花朵。这种颜色比大叶子的银莲花更接近红色了,但“阿童尼斯之血”则不同,人们说,这种银莲花是维纳斯女神的泪水变的,她一边寻找阿童尼斯一边流泪。如此说来,那可怜的女人哭成了什么样儿啊,因为地中海周围的银莲花就像英国的雏菊那么普遍。 这里的雏菊也开了,张着红嘴儿,开得如火如荼一片。最初的花儿大朵大朵的,很壮观。但随着三月一天天过去,它们变成了亮闪闪的小东西,像小纽扣儿,一团团的。这意味着,夏天快到了。 红色的郁金香在麦田里绽开了,很像红罂粟,只是红得更甚。它们说凋谢就凋谢了,从不重新绽放。郁金香花期很短。 在有些地方生长着一些奇特的郁金香,颀长、尖削,像中国人的模样。这种花十分可爱,泛黄的花蕾出挑得纤细尖削。这种花会迅速打蔫,横陈地上,幻影般地消失。 郁金香谢了以后不久夏天就来了。下面该说说夏天了。 四月底这段花的间歇期里,花儿似乎在犹豫,叶子趁机长了起来。有一段时间,在无花果赤裸的树梢上,喷涌而出的绿色就像绿色的火舌在烛台架上燃烧。现在这些喷涌的绿色蔓延开来,开始长成手的模样,摸索着夏季的空气。叶子下是小巧的无花果子,看似羊颈上的血管。 有一段时间里,僵硬如鞭的长藤上结着一些疙疙瘩瘩的粉芽儿,似花蕾一样。现在这些粉芽儿开始舒展出一片片半闭着的绿叶子来,叶子上布满了红色的叶脉,还有尖尖的小花儿,好比一粒粒小种苞。这藤上毛茸茸的粉红小花儿散发着淡淡清香。 山上的杨树长势很好,叶子呈半透明,上面布满了血色的叶脉。它们呈现出金棕色,但不像秋天的那种,更像蝙蝠薄薄的翅膀在夕阳辉映下的乱云中扑闪;夕阳的光辉透过舒展的薄翅,映得那翅膀像沾了棕红色斑的薄玻璃。这就是夏日富于活力的红,而非秋日惨淡的红。远远望去,那些杨树上苏醒中的叶子微微喘息着,闪烁着光芒。这是春天那柔弱的美。 樱桃树情况也大致如此,不过皮实得多。在这四月的最后一周里,樱桃花依然是白的,不过在萎缩、凋谢着,今年算晚的了。树叶繁茂,在血红中泛着微微的古铜色。这个地区的果树真叫怪。梨花和桃花同时绽放。不过,现在梨树已是一树茂盛亮丽的新绿,十分可爱,青苹果一般翠绿生动,在田野里的各种绿色中闪烁着光芒:艳绿的半高麦苗,若隐若现的灰绿橄榄,深绿的柏树,墨绿的常绿橡树,波浪般翻滚的油绿的意大利五针松,浅绿的小桃树和小杏树,还有皮实嫩绿的七叶树。纷呈的绿色,一抹,一层,一片,在坡地,在山峁,在叶尖,在花梗的断茬上,在高高的灌木丛中,绿,绿,傍晚有时亮丽得出奇,田野上看似燃烧着绿色,闪着金光。 风景中,梨树可算是最绿的了。麦苗或许会闪金光或泛着绿色的光芒,但是梨树的绿则是自身的绿。樱桃树上白花儿半开半闭,苹果树也是这样。李子树长出了稀稀拉拉的新叶子,令人难以察觉,杏树、桃树也是这样,风景中几乎难以看得到它们了,尽管二十天前它们一身粉红的花朵在整个乡村中最为耀眼。现在它们的花儿谢了,此时是绿色的时间,绿得夺目,一丝丝,一块块,一片片的绿色。 树林中,矮橡树刚刚稀稀拉拉地抽枝,而松树还在冬眠之中。这些意大利五针松是属于冬天的,圣诞节期间,它们那浓重的绿云十分美丽。柏树那高大赤裸的躯体呈墨绿色,紫皮柳在蓝天下泛着生动的橘红,田野上一片淡紫。冬天的田野上涌现着色彩,景色也十分美丽呢。 可是现在,夜莺依旧发出悠长、渴望而哀怨的叫声,随之又发出快活的鸣啭。松树和柏树看似坚硬粗糙,树林失去了其微妙与神秘。这幅景象仍旧像冬季,尽管稚嫩的橡树在渐渐泛黄,石楠开花了。但是坚硬灰暗的松树在上,坚硬灰暗的高高石楠丛在下,都是那么僵硬,在抗拒,与春天的氛围很不谐调。 尽管这白石般的石楠丛中已是一片落英,看上去也很可爱,可如果随意地一瞥,它就是让你觉得没有花。特别是当白霜或白色灰尘笼罩着它的花冠叶尖时,这种印象就更甚。在一片黯淡无色的树林中,这些花就显得特别苍白如鬼影。这景象令春天的感觉全无觅处。 这高高的白石楠丛虽然黯淡,但的确可爱至极。有时它能长一人高,嫩叶高耸,影子般的“指头”在深褐色的灌木中间长得十分丰满,阳光下的石楠丛散发着甜丝丝蜜的味道,如果你抚摸它,会摸一手细细的白石灰粉。凑近看,会发现它那小小的花铃铛最美,娇小的白花儿,花心儿里生着棕紫色的“眼睛”和细若针鼻儿的雄蕊。在树林外的丽日碧空下,石楠丛长得高高大大,暗白的嫩叶挺立着,旁边一片开满金灿灿黄花儿的野豌豆,这景色着实像被施了魔法一般。 尽管如此,这遍地开花的暗白石楠在这春夏之交时只能加剧松柏林的灰白苍老感,是这个过渡时期的憧憧鬼影。 这倒不是说这一周里见不到花朵,只是这些花儿稀稀拉拉的,显得孤独了些:早开的紫兰花,红扑扑、活泼泼的,你会偶尔看到;一小簇一小簇的蜜蜂兰花,它们对自己参差不齐的外表毫不在意。还有巨大的粗壮密实的粉红兰花,其巨大的穗状花蕾像肥实的麦穗一样坚硬,呈紫色,实在漂亮。不过一些穗子已经绽开了口子,其紫色的花蕾中已经垂落出娇嫩的小花瓣来。另有一些十分可爱的高档奶黄色兰花,长而嫩的花边儿上点缀着棕色的斑点儿。这些花儿生长在较为潮湿的地方,生着古怪的柔软花穗儿,很是鲜见。再有一种是娇小开黄花儿的兰花。 但是,兰花并不能造就夏天。它们过于清高寡合。蓝灰色的飞蓬长出来了,不过还不足以显山露水。以后在炽烈的阳光下它才会猛然引人注目起来。在一条条小路的边沿上,开着成片的玫瑰色野百里香。就是这些,只是初见端倪,还算不上露出了真面目。再等上一个月,才能看到盛开的野百里香呢。 蝴蝶花也是如此。在上边的梯田边沿,在石头缝儿里,绛紫色的蝴蝶花蹿起来了。这花儿美,但几乎算不得什么,因为数量不多,还被风撕扯得不成样子。狂风从地中海那边强劲吹来,虽然不冷,可是一路风驰电掣,着实摧残了这些花儿。片刻的安宁之后,又有强劲的风从亚德里亚海横扫而来,这阵刺骨的强风刮得让人心寒。深紫色的蝴蝶花在这两场风的夹击下瑟瑟抖动,蜷缩着,似乎是受了火烤;而娇小的黄色岩生玫瑰则在细弱的枝头摇曳,后悔自己急于绽放了。 真是急不得。五月份大风就会停的,强烈的阳光会停止其摧残。随之,夜莺会不停地歌唱,而不怎么出声的谨慎的托斯卡纳布谷鸟也会时而发出鸣啼。淡紫色的蝴蝶花落英如瀑,尖长的花瓣儿显得柔美而自豪,开成一片紫烟,开得处处亮丽。 蝴蝶花是一种半野生、半栽培的花。农民有时挖掘其根,还挖掘香蒲根(香蒲根粉这种香料我们仍然在使用)。所以,在五月里,你会发现岩石上、梯田上和田野中有挖掘过的地方闪烁着紫光,弥漫着香味,但你不注意它,甚至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是蝴蝶花,在橄榄花若隐若现之前蝴蝶花开得最盛。 一簇簇的蝴蝶花将开得满山遍野,透着自豪和柔美。玫瑰色的野生唐菖蒲开在麦地里;五六月间,麦收之前,黑种草绽放出蓝色的花朵。 但现在既不是五月,也不是六月,而是四月底,是春夏之交。夜莺时断时续地唱着,豆花在田野里凋谢,豆花香随着春天逝去,小鸟在窝里孵蛋,橄榄剪了枝,葡萄下的地也耕过了,暮春的耕作完活儿了,手头没什么可干的了,再干就是等约两周后收豌豆了。到那时,所有的农民都会蹲在豆畦之间收豆子。豆子丰收的季节很长,能持续两个月呢。 天道变了,不断地变,变得快。阳光普照的国度里,这种变化比起阴沉的国家显得更生动更彻底。在晦暗的国度里,天总是阴沉晦暗,变化稍纵即逝,难以留下真正的印记。在英国,冬季和夏季在阴影中交替。但在这表象之下,是灰暗,永恒的寒彻和黑暗,球茎生存于此,现实就是球茎的现实,这东西富于韧性,积聚着能量。 但在阳光普照的国度里,变化是真的,永恒则是假象和狴犴。在欧洲北方,人们似乎本能地想象,认为太阳像蜡烛一样在永恒的黑暗中燃烧,总有一天这蜡烛会燃尽,太阳会耗尽,于是那永恒的黑暗便会重返。于是,对这些北方人来说,这个现象世界根本上是悲剧性的,因为它是暂时的,必然要终止其生存。其生存本身就意味着停止生存,这是悲剧感的根源。 但对南方人来说,太阳是主宰,如果每一种现象实体都从宇宙中消失,世界上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灿烂辉煌的阳光。太阳的光明是绝对的,阴影和黑暗是相对的,不过是介于太阳和某种东西之间的东西罢了。 这就是普通南方人的本能感觉。当然了,如果你开始理性分析,你会争辩说太阳是一个现象实体。它存在了,还会结束其存在,因此说太阳本身是悲剧性的。 不过这只是个论点而已。我们认为,因为我们要在黑暗中点燃一根蜡烛,所以必定有造物主在太初无边的黑暗中点燃了太阳。 这种论点全然是短视的、肤浅的。我们压根儿不知道太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也根本没有理由假定太阳会结束其生命。我们凭借实际经验知道的是,阴影产生,是因为某种物体介入于我们和太阳之间;当这个介入物移开,阴影停止存在。所以,在经常纠缠我们存在的所有临时的、过渡的或注定要停止的东西里,阴影或黑暗是纯粹暂时的。我们可以想想死亡,如果愿意的话,把它看成是介于我们和太阳之间的永恒之物。这正是普通南方人对于死亡的认识基点。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太阳。经验告诉人们,人类认为永远不朽的是灿烂的太阳,黑暗的阴影只是一种偶然的介入。 这样一来,严格地说,就没了悲剧。宇宙中没有悲剧,人之所以富于悲剧性,是因为他怕死。对我来说,只要这太阳永远灿烂,无论有多少字词的云翳遮拦,它都永远光辉灿烂,死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在阳光下,甚至死都充满了阳光。阳光是没有完结的时候的。 因此,在我心目中,瞬息万变的托斯卡纳之春全无悲剧的意味。“去年的雪在哪儿呢?”嗨,它们该在哪儿就在那儿。八周前的小黄乌头花儿哪儿去了?我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它们充满了阳光,阳光在闪耀着,阳光意味着变化,花儿谢了又开了。冬乌头花灿烂地开了,又携着阳光而去。还有什么?太阳永远灿烂。如果我们不这样想就错了。 译者注:原文共四节,但除剑桥版的劳伦斯散文选外,所有其他选本都只选入前三节,舍去游离了托斯卡纳和花之主题的第四节。故译者随俗只翻译出前三节,特注。 #Julian书友会# 劳伦斯就是这样随意 散文可以无限散 虽然第4节没有翻译 但这3节已经没到不胜收 ... 周末好书分享 与书友们共赏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eizhongcaozia.com/hzczhxcf/38522.html
- 上一篇文章: 2018225云南昆明斗南拍市花花
- 下一篇文章: 每天抹一抹,7天止脱,30天生发,秃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