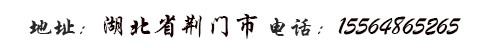吐尔孙艾拜从中专到清华园,无论走了多远
|
编者按 年,吐尔孙·艾拜出生于一个温馨平静的南疆小城。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故乡也许是一种情感上的羁绊,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但最终变成了民谣里吟唱的那样,成为「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但对吐尔孙而言,故乡可不是这么容易割舍的。 吐尔孙·艾拜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西北,扎根基层,31岁又重返清华园读博。他的故事或许是众多清华学子中平凡的一个,但平凡中体现的是清华人脚踏实地、心系基层的可贵品质。 吐尔孙·艾拜出生于一个温馨平静的南疆小城。父亲供职于当地银行,母亲在家中料理家务,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和美。 虽然全职居家,但吐尔孙的母亲所做的可远不止洗洗刷刷,她出身于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当时为数不多能读能写的女性。这一优势也使她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当国有企业响应党的「五七」指示开始扩招工人的时候,她经过严格的审查成为了一名「五七工」,从小镇走到了县城,成为了一名羡煞旁人的「工人」。这段经历使她一生对教育怀有一种宗教感情般的热忱,用她的话说就是,「我不相信命运,但我相信知识。」 她将这一信念贯穿到了对吐尔孙的教育中。早在入学之前,母亲就已经教他识字和简单的算术,后来更是费尽周章将他送进全县最好的小学。现在听来,这一切似乎稀松平常,毕竟大多数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决心,用「倾家荡产」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疆,当时人们可不认为教育能改变命运,能读能写即可,有劳动能力的孩子继续在学校闲逛无疑是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吐尔孙母亲在教育问题上的坚持,不单单是一种决心,实在称得上远见卓识 小吐尔孙也不负母亲所望,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孩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将有机会继续升学,母亲曾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农村走到了县城,他则能在母亲的起点上走得更远,「向城市进发」的征程将在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 可惜没如果。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所有伟大征程都戛然而止,「幼年丧父」四个大字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线。原本富裕殷实的一家人现在突然要靠抚恤金和低保过活,母亲开始为几毛钱在菜市场与商贩争执,吐尔孙的少年时代也在孤独、黯淡和纠结中草草收场。 一个大胆的决定 年,世纪之末,吐尔孙决定把自己当年的憧憬尘封在旧世纪里。父亲的离世让他早早学会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放弃梦想的确让人心碎,但如果是为了家人,那一切就不是那么不可接受,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了莎车师范学校,期待能够早点毕业、工作、养活母亲和弟弟。 不巧的是,待他毕业时,刚好赶上自治区政策大调整的时期,政府不再统一为中专生分配工作。新旧政策交替打乱了那批毕业生的步伐,他们本来离「国家铁饭碗」只有一步之遥,现在却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很多人迷茫而不知所措。 如果说上帝真的在掷骰子,好坏也是五五开,他塞给人的惊喜,往往和砸在人头上的不幸一样厚重。在家待业三个月后,吐尔孙做了一个外人看来十分癫狂的决定:他决定去高三复习班备考大学。在中专学习的三年里,从来没人告诉他怎么通过光照图判断南北半球,更没人教他怎么计算椭圆的离心率,空降高三直接备考,个中艰辛,绝不是励志电影里的几个蒙太奇镜头可以描述清楚。 为了能够静心学习,他将家中的地下室隔成两截,一边做书房,一边做卧室,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他的所有时间都在这个密室中度过。他甚至没给自己设置固定的睡眠时间,累到了极点就趴在桌子上睡,睡醒了继续学,几乎到了以生理极限安排生活作息的程度。此外,中专生涯也并非毫无用处。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中专生一毕业就要参加工作,他们被视作能够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而非少不更事的高中生。这让吐尔孙迅速完成了心里蜕变,他已经不需要任何高考动员大会,不需要任何人苦口婆心的劝导,深深切切地知道他是在为自己而奋斗。 这份早慧足以使他在高考中异军突起。在一整年暗无天日的高强度学习之后,他一跃进入班级前三甲,获得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又一路高歌猛进,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当初那个大胆疯狂的决定,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美丽新世界 维吾尔族青年、名校高材生,多重特殊身份加持,使吐尔孙的求学之路注定不同一般。 语言是第一重障碍。就语言环境而言,从新疆到内地学习,跨度不亚于内地学生出国留学。吐尔孙惊奇地发现,当自己与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偶尔地,他们会不合时宜地对着他微笑点头,却不做任何言语上的回应。很久以后,朋友们才告诉他,原来在那些沉默的时刻,他们压根没听懂吐尔孙在说什么,又不好意思明说,只能微笑地点头表示善意。这样尴尬的聊天模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吐尔孙认识了一个北京女生,她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向他展示了汉语的平仄顿挫,吐尔孙的汉语水平从此得到了质的提升。 语言只是求学路上的第一道关卡,不久之后,吐尔孙发现了自己和内地同学的真正差距在学习方式上。他发现身边的同学似乎对考试重点有精准的直觉,而且懂得制定长期规划、短期目标,其高超的猜题能力、高效的时间管理策略,让吐尔孙叹为观止。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吐尔孙显然明白这一点,他会细细地观察学习,也不耻于开口请教,如同八角章鱼伸开触手扑向猎物一样,他也打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来吸纳新知识。 在进入内地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除了偶尔被认成外国人,吐尔孙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环境,他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在专业学习上也毫不逊色,甚至还学有余力地修了法学双学位。 「我们在入学时也许受到了政策照拂,但坚决地拒绝了学校降低毕业标准的好意,我们想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毕业生」,他的骄傲不允许自己顶着少数民族学生的帽子滥竽充数。 平稳过渡之后,是时候有所建树了。 年,吐尔孙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时正是乌鲁木齐7·5打砸抢暴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打开维吾尔语网络一看就被惊呆了,发现很多维语网站被境外势力利用,充斥着扭曲我国民族政策的不实言论。作为一个新疆学子、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青年研究者,此番混乱状况让吐尔孙受到了很大冲击,他决心为此做点什么。 博一那年,机会终于来了,吐尔孙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介绍了维语网站的监管现状后,在场学者感到相当震惊,他们没想到维语网站竟如此暗流涌动,十分关切地敦促他要把这个研究做下去。在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吐尔孙组建了一个专题调研组,往返于北京和新疆各地,深入挖掘维语网络的问题,最后撰写了报告《维吾尔语网站现状、问题和建议》。这一报告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批示,对新疆的网络监管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新疆的孩子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故乡也许是一种情感上的羁绊,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我们会深情地咏诵诗句去赞美她,却绝不甘愿为之奉献一生,我们会为了更好的发展机遇而远走他方,故乡最终变成了民谣里吟唱的那样,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但对吐尔孙而言,故乡可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割舍的地方。十余载求学历程中,他受到了诸多照拂,无论来自国家民族政策还是师长好友,这些额外的关怀与他的民族身份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受恩与报恩的过程,如同吐尔孙的老师史宗恺对他说的: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 新疆于他而言,如同命中的磁石,所有的离开,都是为了更好地归去。 今年年初,吐尔孙主动要求从新疆团校下派到和田县巴克敦村参加驻村工作。他说自己热爱新疆的大美河山,为那里的人们修路架桥,亲眼见证自己的工作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变化,这种满足感实在千金不换。 吐尔孙驻村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劝学,劝青年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劝乡民学习汉语。他深知自己的人生转轨得益于教育,而他对教育的信心源于母亲。他希望能把这种信心继续传递下去,因此经常村民分享自己的求学故事,讲述当初的决定如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希望他们能透过自己看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文字工作者,他也写文章向更广大的受众分享自己的故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一文。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的求学工作历程,号召维吾尔族青年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科学文化知识,为自己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疆学子中引起了广泛共鸣。 当然,基层工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田园牧歌的诗意生活。生活上的清苦自不必说,它还意味着繁琐的村务杂事、长时间的单调无趣,很多人的意志都消弭于半途,只盼这场苦行能早日结束。吐尔孙当然也能感受到这些负面情绪,但早年的经历使他对苦难有非同寻常的耐受力,流淌于清华人血液中的家国情怀也能够帮他驱散塞外深夜的寒意。另外,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不也是一版铿锵的诗意人生。 来源:清华研读间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eizhongcaozia.com/hzczsjkz/62436.html
- 上一篇文章: 阿勒泰支教日记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
- 下一篇文章: 2021大美新疆旅行笔记NO14喀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