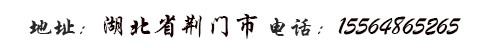我与几只田园犬的交往史
|
原创居晦人间故事铺 对于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宠物”这个概念是模糊的。许多人家中会养狗,大多是“中华田园犬”。它们既是看家护院的好帮手,也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伙伴,这样复杂的身份很难以“宠物”一词囊括。没有细致的喂养方案,没有高级的狗窝狗盆,这些其貌不扬的土狗,陪着主人走过无数个四季,成为回忆里最干净纯粹的一道光。 人间故事铺 storytelling 疫情之下,所属单位前一天通知解除封控,市里却在第二天开展封控。无奈,只有留在老家。 夏日家乡清爽得很,村里除了老人,再无情趣。于是上山下河,重温旧梦。家中新入两只田园犬,尤其与人往来密切,在疫情高压之下给人些许慰藉。 有人传言狗会吃鸡或者恶意将鸡咬死,我以为惊异;知道事实与之截然相反,忽又联想到疫情之下众生百态,谣言迷离,扰人清心。 从来,狗是人的忠诚伙伴之一,几乎任劳任怨。既有护卫本领,又可解人心烦,竟然受此谣言,但不可自己反驳。细细想来,狗对我之陪伴,也是一种长存的感动,愿意为之正名,便写下此文,以此纪念和为它们廉价的好意做一点保护。 望大家不轻易丢掉或遗忘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守护,在任意时空里,能够用存在的余温持续燃烧生命的火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我所知道的农村里,家家户户几乎是要养上或养过一只及其以上的中华田园犬。这样的狗又被称作“土狗”。我肤浅觉得,它们与警犬相比,不过是缺乏专业的训练与教导。田园犬护卫小家的本领,让我衷心为之赞叹。可是长久以来,俗物难登大雅之堂。但我实在以为,人的偏见眼光是不能遮住灵物的光辉的。 1 位于川北的小村子,是我的家乡杨家沟。山高,河小,路窄,地陡。主要的小商品产物是玉米,土豆。杨家沟地处秦岭以南,同时落在高山之上。人们主食为米,面食为辅。 每户村民每年要打出上千斤的成熟玉米籽去卖钱,然后用来买米置衣、供娃上学。另外就是养猪,放牛,饲鸡。猪是主要肉食。鸡只是过年或逢遇大事的时候才能吃上,且数量限制在一只或两只。牛是主要劳力。后来,有人听闻传言或确实某家遭遇偷窃,为了更好保障财物安全,大家流行养起了狗。 我在出生之后,家里有一只十多年的大黄狗。体毛细长而茂盛,方正的脑袋,粗实的四肢,大尾巴常常上翘着,母亲唤它“黄狮子”。 那时候母鸡所生的小鸡是黄鼠狼或山鹰的食物来源之一,父亲又常年在外打拼,母亲一个人难以招架。黄鼠狼狡猾得很,喜欢半夜搞偷袭。山鹰更是厉害,它会趁人做其他农活的间隙,迅速从天而降,叼走一只鸡仔然后匆匆离开。黄狮子死后的空档期,我还专职做过一段时间的护鸡工作。 黄狮子不是天生的全能警卫,纵有一身本领,大多只是施加在“生人”身上。其他牲畜受到侵害,它并无太大作用。于是,母亲开始花时间下工夫训导它。后来,出于本能和后天学习的双重因素,家里不论谁,只要对它命令一句“快脚!”它便能立刻专注地竖起双耳,跑到院子边来回巡视一次,嘴里同时发出低吼,以示警告。 我们家穷,人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狗的温饱条件相比村里其他看家犬,也处于下等。种粮换取的资产常年供不应求。母亲一个人一年辛勤耕种的十几亩地,换取的钱资每到年底都不知去向。家里过年的成员在六七年内只限于我,姐和母亲。父亲会打回电话,装作很轻松地跟我和姐姐说几句祝福语,接着跟母亲交代的核心意思:“没挣到钱。”所以不会回来。 夜里,我们三个人可以看电视到半夜。黄狮子也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肉汤泡饭,夜深,便在房檐之下蜷缩着睡觉。 “狗不嫌家贫”,黄狮子并不会和其他家的狗到处乱窜。它的体型是村里同类中最大的,这成为它不合群的一个原因。 有一回母亲被央到别人家帮忙栽苞谷,我放学后就在东家吃饭。每到这种时候,人们聚集一家。狗也凑在一起,在两个大餐桌下捡骨头吃。东家比平时更通情达理,对于在位的帮助者们格外客气友好,连同各家的狗们也受到优待,全部气氛是和平而且热闹的。 或许是因为一块骨头或者一片肉的争端,黄狮子和杨三爷家的黑毛狗发生了直接冲突。黄狮子把黑毛狗从饭桌下追出来,它的右前腿被黄狮子紧紧咬住。其他七八只狗闻声,跑过来帮黑毛狗打架。顷刻间,狗声盖过了人声。 东家忙跑出门把它们喝开,几个在外吃饭的男人寻找石子或木棍对着狗群一顿乱打。狗群暂时疏散开来,转瞬之间,又追赶黄狮子转移到半山坡上开展咬架。 我赶紧进屋告诉母亲,母亲放下碗筷,抓起地上的石子对着狗群狂扔过去,一边怒骂着这群土匪。 黄狮子和其他狗的关系虽说不好,但我的印象中,还未见它有过“欺狗”的行为。“打狗还得看主人”,狗能受此待遇,大约与我们的家境有关。父亲挣不得钱,母亲即使守在家里兢兢业业,囿于爷爷对她的轻视,婆婆对她的排挤,其他女性对她的蔑视,我们家也成了众矢之的。 “你打我们家的狗弄啥?”一个男人质问母亲。 “那些狗都在咬我们那狗,咬死了多可惜。”母亲辩护道。 “你们家那狗,又好吃又霸道,所以那些狗都对它不舒服,你还不晓得这个道理?” 母亲看着颈毛上沾满血渍的黄狮子,怒斥它立即回家去。 自此以后,黄狮子得了一场大病,整日在家病恹恹的。母亲让我去找爷爷说拿点药,或者来家里给它诊一诊。 “我以后老了让你给我倒杯水,不晓得是个什么效果!”我当时不懂这话,一心只想拿药。 药拿回去,母亲把它和在饭里,唤黄狮子来吃。它懒懒地走过来,低垂着头,我在旁边侍候它。它情绪低落,我用手搅拌饭团,想把药粉拌匀,让黄狮子看不见药的痕迹。 忽然,“嗷”地一声,它一口咬向我的食指。我吓得大叫,手指已经流了血。母亲慌忙出来,不停呵斥黄狮子,骂它“遭了瘟”。狗受了惊吓,不知所踪。我随母亲去找爷爷包扎,他怨言黄狮子是喂不熟的野狼。 夜里,黄狮子没有回家。母亲把饭端在手里,唤了许久,仍不见它的身影。第二天下了一整天暴雨,积水各成一道,汇在路面,山坡,地里。黄狮子依然没有踪迹。 “狗应该是死在哪儿了。”母亲推测说。 第三天还是雨,不过较前一天下得小了一些。去山里看护庄稼的三婆路过我家对母亲说:“你们家那黄狗好像死在了杨三老汉的地里,你去看看吧。” 母亲拿了一把锄头,让我换上水鞋,带着一只撮箕。我们身穿雨衣,关了房门,快步赶往黄狮子死去的方向。 到了小道边,黄狮子的头栽在水沟里,全身僵硬而冰凉。母亲唤它一声,再摸了一把肚子,断定狗的确死了。她让我把锄头接过去,自己拽着黄狮子的后腿往外拉。拖出整个身子后,就提着它的四腿奔向山上。 乌蒙蒙的天,雷鸣电闪,我怕经过松树下面被雷公“抓了去”,紧紧跟在母亲身后。 到了我家山林的一棵大松树下,母亲开始掘土,一撮箕接一撮箕地把土堆在外边。她不停地挖着,一声不吭。 “妈,为什么不埋在地里?”我问母亲。 “山下没我们家的地;埋在这儿,也免得其他狗刨土。” “妈,天上打雷了,我们老师说下雨天不能站在……” “话不要多。” 母亲挖出一个大小合适的土坑,把黄狮子的尸体安稳地放进去,然后给它盖上湿土。刚刚掘开的泥土又重新回到原地,母亲用锄头将土层压实,铲下几根草枝和刺杆,横竖盖在黄狮子的坟上,又在周围放下几块石头压住枝头。 “走吧。” 我随着母亲回了家。从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没人再说我们家的黄狗是如何招人厌恶,家门前后本也没有生长可供指代的槐树和桑树,日子无意之间,安宁了不少。 几年后我爬上那座大山,经过小路,发现那棵松树越发壮实。树下的枝丫石头早已不复存在,但我知道,我家的黄狗就埋在那里。 2 我们家是平房,有一间屋子的后门通往厨房。一天,天色刚刚擦黑,母亲去柴房拾柴,给鸡门上锁。她没打算关后门,因为还要把柴火顺便搬进屋子。不到十分钟,家里就少了一整块猪蹄和排骨。母亲四下察看,也是徒劳。即使抓到现行,以母亲的意思,“冤家宜解不宜结”。 假设有一只狗看家,小偷是不敢那般肆意妄为的。母亲有意逮一只狗继续养着。 一个暑天的傍晚,我和母亲下地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户人家的几只狗朝着我们吼叫。母亲停在原地歇气,朝狗群叫了一声“黑子”。有一只叫声稚嫩,形体娇小的黑狗便向她甩尾巴。母亲又唤了几声,它就跑到院子边,左右摇着小脑袋察看我们这一对陌生人。 “这狗好看吗?” 我见它模样可爱,不怕生人,而且勇敢亲和,满口喜欢。母亲说过几天会把它逮回家喂着。 黑子成了我们家的新任警卫员。它的耳朵尖长而有力,稍有风吹草动,一双黑耳瞬间警觉地直立起来,水灵的眼珠子也十分警惕地盯向生出动静的方位。胸部直到下颚骨的区间,是一片永远白色的绒毛,从未见它染上别的颜色弄脏它们。它的四只脚背,下巴以及尾巴尖也缀着白花。单从模样来说,它是我迄今遇见过最出挑的土狗。 它喜欢和过路的摩托赛跑,但不会攻击驾车的人,而是边追边吠叫着示威。村里的小孩们就编了一句顺口溜“狗追摩托,不懂科学(xio)”。父亲没买车之前,走亲戚、办事,都是骑一辆摩托车。黑子也要跟着去的。临走,我坐在摩托车上,父亲的速度并不快,它就跟着后面跑。距离短的路程,它会一直跑回家,然后停着休息,张嘴伸出舌头散热。 一个冬季,路面结了冰。黑子听见摩托车慢吞吞的声音,顺着习惯仍要与之竞跑。那男人大约是不善于在冰雪路面骑行,手脚一慌,连人带车翻在硬路面上。黑子站在路边,摇着尾巴,仿佛是致歉。男人驮着的一袋米被打湿,小腿擦破了皮,一边努力站起身子扶正摩托,一边叫骂养狗的人家。 父亲最怕亏心事。赶忙跑到路上,斥骂黑子离开,又给人家赔礼道歉。硬要拉着男人到家吃饭,还塞给他两百元作为赔偿。好在男人与爷爷熟识,勉强到我家用了午饭。父亲又给他喷了碘伏,塞给他一包玉溪。他便大方地离开了。 事后,父亲把黑子叫到身边,用细竹棍一下鞭在它的后腿上,训诫它不准再追赶任何车辆。之后,黑子只是跟着自家的摩托车驰跑,对马路上的过往车辆失掉了原有的兴趣。 每逢过年,三十夜里,家家户户都要先放鞭炮再开年夜饭。父亲至家第一年,家里买了一箱八十八响的大地红烟花,准备年夜饭后点燃观赏。别家的狗估计是耳朵受不住,一律被鞭炮震得钻床底,抑或胡乱跑到山上不肯归家。黑子反而极其勇猛,非但不以为惧,而且连蹦带跳地在响声之中狂呼大叫。 黑子的灵性逐渐引起人们兴趣。父亲平时爱干净,我只要跟黑子走近一点,他就要急切严肃地发议论:“狗身上有细菌!”我只好姑且与它保持距离。不过,他当着别人的面以狗做谈资时,就要说:“我几年没回家,第一次踏进家门,狗居然朝我甩尾巴。” 父亲多少在外卖力实干了几年,挣得一点家业。闲来无事到家做客或者串门的人,便会将黑子的奇特作为一种敬意搬上桌面聊白几句。 “我到你们家拿一个锄头——我给你妈打过招呼的——你们屋里这黑娃子,就扑过来衔住我的裤腿,不让我走。我把东西放下后,它才准许我离开。我于是另找主意,叫你爹亲自帮我拿到手。我还没见过哪家的狗这么灵气。你说它又不是真的要咬我,但它执意用嘴拉住裤腿……” 于是大家哄笑一场。此时我去拍拍它的头,或者从碗里喂给它一片肉,父亲是不会皱眉的。 我到了七岁才上小学,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只有一学期学前班。黑子自发地陪送我去村小。学校的日程安排是朝九晚五。早晨,我要在家吃完一大碗米饭,再去上学。学校没有食堂,只有小卖部。父亲彼时依然在西藏奔波,母亲每天至多给我一块钱的零花钱。有时候没钱,我会带上做好的清油炒米饭或者油煎的土豆馍,当做午饭。 当时所有的小伙伴里,唯有我一人享受贴身保镖的殊荣,大家好不羡慕。到了学校,班上的同学看见黑子的模样,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围成一圈逗弄它。有时三三两两的路过,也要去摸一摸它的头。它倒也乖巧,或许是大家对它毫不吝啬地投喂所致。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上课铃声响后,大部分人回到教室。语文老师一进门,我们顿时安静下来。开课之前,从外面忽地传进几声惨烈的狗叫,我心里一颤,料想定然是黑子被什么人给打了。几分钟后,同桌从厕所跑回来,对我说:“你的警犬被冉老师(数学老师)打得跑丢了。” 下课之后,我急忙跑到数学老师规定的操场界线查看——那是连接外界与操场的一条横线,学生上课期间不允许跨过那条线走上马路。我呆立着,探寻黑子的轨迹,它却没有再出现。 周五的下学时间要早过平时。学生们做完大扫除,三点就可以离校。放学过后,我没有等待任何伙伴,一路狂奔回家。走到桥下,爷爷在院子边上扫地,我便问他,狗回家没有。他说黑子在他们家。 我从小路跑上去,嘴里唤着黑子的名字。它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我。进到屋里,它卧在猪草垛上睡着。我轻轻蹲下身子,抚慰着它垂下的头。黑子终于抬起头来,右眼珠子变成了鱼肚白。爷爷告诉我说:“狗的右眼瞎了。” 我痛苦而绝望,搂着黑子的脖子,把脸贴在它的头上大哭一场。黑子的表情显得轻松,似乎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给它道歉,吃生鸡蛋,它全程异常安静。以后,黑子不再送我上学。我为它的受伤憎恨数学老师到六年级。 经过08年地震的摧残,村小一下老了不少。墙体开裂,瓦碎了一地。几个月没有进行教学活动,平旷的操场长起一寸多深的杂草。乡镇学校打算把所有的留守娃全部并入,统一管理。大部分学生选择去镇上,而我,被安排进城读书。 至于黑子,则托给爷爷奶奶。临走那天,黑子看见我们身着新装,背包在手,隐约之中觉察到我们的离别。它忙前忙后,在母亲身边摇一会儿尾巴,又殷勤地跑到我身旁用头蹭我的小腿。 我拍拍它的头,告诉它我马上要走了,寒假才能回家。其实,前一天晚上我就给它说了这些话,它还不为所动。到了分别时刻,它竟真的不舍起来。我不想就此融入一个陌生之地,大人们是不能理解我的难处的。 母亲和我要步行到另外一个队的十字路口,等待班车,顺路进城。黑子本意要跟随我们走,但被母亲再三阻止。它见状,便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我们走到半路上,黑子突然窜出来,我嚷着要求母亲先不要急着把它遣返。她一路偶尔拍手跺脚,把它吓到旁边。它停了一会,不一会又追了上来。 我们母子二人同一只狗走出了大山。母亲说,十字路口上死狗最多,不是咬架而死的,就是被人打死,随即带回家煮肉吃。我慌张起来,也开始配合母亲打算把黑子吓退回去。 上车后,司机师傅开着超载数人的班车一骑绝尘。我望向窗外,黑子追车跑了一段距离,可绕过两个弯,便望不见它的身影了。 我不知道它的心情是否和我一样失落,更担忧它会被人打死拿去吃了肉。车内本就拥挤,路况又坏,司机全然不顾乘客感受,只顾着飞驰。内外的不快一齐向我开火,我晕车了。 城里高温不退,是我从未体会过的燥热。山上的日子本来清爽,下了城,就另是一番天地。晚上,我给爷爷打电话,问及黑子是否回家。爷爷说它已经到家了,我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下。 我睡在姑姑家的地板上,热不可耐。前一个月我还在村野追风赶月,没想到由于一个秋季开学,我便被淹没在城市的热浪里。 3 母亲和我在姑姑家住了三天,第四天搬入租的一室一厅房子里。房东老爷子一家住在一楼。他们喂了一只白色小狮子狗。我们刚进大门,它就向主人报警。后来成了住户,它也没有改变对我们的敌对态度。有一回表姐来我家吃饭,给它喂了一根火腿肠,在这之后,它见了表姐就摇起尾巴,并卧在那里听凭她的抚弄。 我厌恶它嗲声嗲气的声音,更厌烦见到它龇牙咧嘴的丑相,最不愿面对的,是它完全让人信赖不住的媚态。房东太太跟风让儿子在大门口装上一个监控,哈巴狗看守家门的作用大不如前,但它依旧未曾停止对一切不明动静的狂吠。 到了生疏的环境,我首先持续的情感是,早日回到老家去。我一个人独行,母亲不甚放心:车程花费两个多小时,并要考虑到有无座位的情况。劳动节我想回家,中秋也想回去。到了国庆,更止不住想要一下穿越到家里。 父亲在我和母亲进城后很快回到城里。他对我的要求严格而多样。比如,星期五我跟母亲商量是否可以回老家,得到她的允许后,第二天父亲却持否决态度。要么是嫌车费太贵,时间来不及,要么是觉得我的安全无法保障。在父亲看来,我的差等生成绩也没资格提出诉求。 我几乎是半年才能回家一次。每次跟爷爷打电话,我第一时间就是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eizhongcaozia.com/hzczhxcf/62277.html
- 上一篇文章: 冬吃萝卜好处多,这5种萝卜的做法请收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