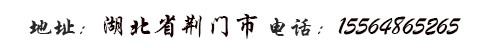芦苇,你好刘丽莹原创作品5
|
北京专治痤疮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yqhg/210111/8578752.html 当思念已老成我褪色的容颜,请敞开你温暖的怀抱,大芦苇,你依然开得苍茫,我依然爱你如初。 ——题记 一 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脑海里都会有一幅画,一幅镌刻着家乡某种意像的画。 我脑海里留下的家乡的意像,是芦苇。 每次小别故乡,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冬日的暮晚,淡红色的落日收敛了余光,孤独地挂在苍冥的天边,无垠的草色给空旷的原野涂上无限的苍凉,而这北方肃杀的空旷里,总会有那么一片、一簇、甚至是一株芦苇,倔强的在风中起伏,目不斜视温情的望着夕阳。带着仆仆风尘归来,看到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芦苇,眼前突然一亮,仿佛看到了站在路边迎候的亲人,一瞬间涌起的心绪,温柔而又苍凉。 或许,这并非是我一个人脑海里的画面。 这是辽河三角洲腹地。若问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接触最多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几乎会听到同一个答案——芦苇。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小到大,一年四季,甚至一辈子都没离开和芦苇打交道。辽河、大辽河、大凌河、双饶河、太平河等大小21条河流交织汇聚,留下了这块世界最大最美的湿地。 湿地,科学上说是介于水陆之间的特殊生态系统,专家用唯美的思维称其为“地球之肾”“天然物种库”“天然水库”。而当地人则用现实的思维大称其“大沼泽”“大洼塘”。 这偌大的地球之肾偏是盐碱含量颇高,并不适合寻常植物的生长,或许在其他地方,鸟儿随意丢落的、粪便里边的一粒树籽,都可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在这里,即便是精心呵护,也未必长好一颗树苗苗,这可让不惧苦寒咸涩的芦苇,成了盐碱地上的先锋植物,在广阔的滩涂找到了自己的天堂。 芦苇择水泽而生,给阳光就灿烂,不用照拂,无需眷顾,以根状茎繁殖为主,横走的根状茎,纵横交错形成网状,潜在藻泽,扎在水里,埋在地下,有时根茎层较厚,甚至伏在水面,可禁得住人、畜在上面行走。从滩汀洲渚到坑塘沟渠,从水深几厘米至1米以上水域,一旦条件适宜,便发育成新茎,生出芦苇群落,且一不小心放纵成海,成为亚洲第一苇塘,世界第二大芦苇产地。芦苇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的思索,还没有来得及想好策略的住民,面对如此泛滥的长势,也只好望“苇”兴叹,称之曰“南大荒”。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常理,苇海边上的人自然“靠苇吃苇”。人们在与芦苇长期的同床共枕中,深得其庇佑,被人们亲切的称为“铁杆庄稼”。浩瀚苇田,总会有零星的散田为民所用。春起吃芦根,端午打苇叶,芦苇成熟期可以去做刀客,挣些补给,也可买一些芦苇存用,在农闲之时织席编篓,做些小工艺品去卖钱。小工艺这手头上不经意的玩意,却能瞥见劳动者丰富的内涵,更能感受“劳动”“艰辛”背后的伟大。沟边地头品相不佳的芦苇可用来做床铺、做烧柴。从春到秋,只要有满眼的芦管管,芦花花,就有家的踏实感。 二 其实,茫茫的芦苇荡,就是大自然中一部经典的物语,它的深重与奥秘让人永远读不透。 浩渺、蓊郁的生命之象,干而不萎,枯而不倒。以其飘逸脱俗的意象令人感受时序的变迁,丰富的人文内涵。 古人称芦苇为“芦”(苇、葭)或“荻”(萑、蒹)。除却我们熟悉的“蒹葭苍苍”,《诗经》的“《召南》《卫风》等多篇还写到:“葭菼掲揭”“萑苇淠淠”,不仅给芦苇优雅的形象,还描绘出芦苇长势的旺盛。古时的芦苇长势到底如何,旺盛到何种程度?《淮南子》中有这样的描述“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说的是远古洪荒之时,那时芦苇铺天盖地,女娲娘娘用积攒下焚烧的芦苇灰,堰堵洪流的泛滥。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更泾渭分明的罗列出芦苇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分布,长江、黄河、海河下游冲击平原且有生长。尤其成为北方湿地建群物种,滨海滩涂,沼泽沟渠均可毗邻成片。清中叶以来,东三省芦苇资源始见典籍。嘉庆年间,大臣英和《卜魁域赋》注称“距城东六十里为呼雨哩河(现乌裕尔河),有苇丛生百数十里”,晚清陈澹然称“竟是滨海自旅顺至登、莱弥望皆成萑苇”。芦苇因其生存能力超强,于荒凉恶劣、盐碱斥卤的地方均可落户安家。 辽河口实为退海之地,芦荻落户此地的历史应该是悠久的,遗憾的是,直到清代的史料也未曾见记有“世界最大最美湿地辽河三角洲”的字样。多少人开口便唱“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我倒是很希望改为“辽河入海口,芦荻齐如麻”。 芦苇最初留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肃穆,甚至有些恐惧。 那是我幼年时的一个冬天,我随母亲去苇塘,给即将外出“拉脚”的父亲送干粮。平生第一次到大苇塘,第一次看到芦苇可以这样茫茫无际、连绵无绝,根本看不到天地的切口,我个头矮小,要一直仰着头,眼前只有天空和芦苇,毛茸茸的芦苇花,晃来晃去的,像玻璃擦一样,把天空擦得瓦蓝瓦蓝的。一些割苇人奔忙其中,忽隐忽现的劳作。白日如灯,人如蝼蚁,我顿感掉入了迷宫。父亲正站在高耸入云的苇垛上,如同一只寒鸦,好像一不小心就要被天空掳走,我的心立刻悬浮起来,祈求快些离开苇塘,祈祷父亲早日平安回家。 这种肃穆感来自幼时留在心底的烙印,久久未曾磨灭,以至于后来学到诗经里的《蒹葭》,我的心里仍是十分惶惑,不停的问:伊人,你一会在水之湄,一会在水之涘,一会在水中沚,你就不怕迷路?你就不知道你心爱的人提着一颗心在等你回到他身边? 不过,古人赋予芦苇的那种浪漫情怀,怕是今人也难以比肩。诗中那种柔美、迷离的情境,倒是让我心头对芦苇产生了轻灵之感。这种的感觉还出现在“一声横玉西风里,芦花不动鸥飞起”,“芦苇声多雁满陂,湿云连野见山稀”的诗句之中。细一想,这种绝妙的情境,脑里是有储存的呀!静时可比娇人照水,风动又如四面楚歌,汀煮之上半遮半掩,沼泽之间烟波浩渺。古人赋予笔下的芦苇,不仅有意境的美、姿态的雅,当然更动之以情。 因何古人如此对芦苇一路情有独钟?最靠谱的理解,莫过于——聪明的古人是将“南骚北风”中的这株俗物作为了意象,寄托于文学创作之中,将自身悲秋伤怀之思、漂泊客旅之愁、离情别绪之感和固穷守节之态,付诸芦苇以情感和内涵,借芦苇的物色美感及因时而变的万千姿态,来表达内心的隐逸情怀,或通过芦苇这一文学符号,象征生活积淀过程中种种物象迭生。 我对芦苇印象的改变大约就始于古人这些通灵毓秀的诗句。 青绿,淡紫,嫩生生、水灵灵的。这是密匝匝的芦苇芽儿,钻出来了,铺满沟塘、水泽之上,一望无际、若隐若现,像少女纤细的玉指,将原野沉积一冬的清苦孤独、宁静致远,浓缩成了生机勃发的气息。 在辽河三角洲,芦苇并非春天的先驱,需待清明之后,正所谓“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涉禽、水鸟成群结队的了赶了来,起落翔集,怕也不仅仅是为觅食,而是为这里静谧的春色,增添一些优美的律动。芦苇的长速惊人,“根长一寸,稍长一尺”。这紧裹着的芽尖,要不了20日,就能身高两尺,托出三四叶片,一个月后,俨然生成了茂生生的后生,具有了手拉手、肩并肩的和谐意气,汇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六月是芦苇生长的高峰期,平均每天要长3里米左右,倘若你站在苇海中,倘若你有足够的细心,便真的能听到芦苇拔节的美妙声音。七月末接近成熟的芦苇准备抽穗,同时开始厉兵秣马。它们必须操练有素,才可与风雨雷电抗争。它们不能倒下,不能死去,因为这一期间它们要孕育好“越冬芽”,方可在明年春天让家族发展壮大。 “横塘一别已千里,芦苇萧萧风雨多。碧波荡漾的苇海、纵横交错的水道,构成了一个辽阔、幽深、曲折的芦苇荡世界”,诗人许浑,定是亲历了一次风雨飘摇中苍凉的芦苇,赋予其不折不扣的感情的寄托。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知道暴风雨中的芦苇的坚强与倔强。 那一次,我就站在苇荡中心的凉亭里,风摇得人一不小心就会抛身苇海,而眼前无边无际的芦苇,却如临阵的士兵,肩搭着肩,手握紧手,岿然不动。风暴怒的时候会使出吃奶的劲,肆虐的旋过来,发出瘆人的嚎叫,胳膊粗细的木杆时有被拦腰摧折,不过小指粗的芦苇,却凭它独到的智慧安然无恙。它们先是一波一波,一片一片的顺着风势,间或向前匍匐,全身都匍匐下去,后一波的头碰到前一波的脚,而后再柔韧的凭借风势反弹,高高挺起,他们发出低沉却悠扬的和唱,推送出一轮一轮的苇浪,一直涌向天际,每一轮浪潮都暗涌着为下一刻崛起的力量。 雨,从远处而来,没有轰隆隆的喧嚣,唯听得到进军的鼓角,如即将爆发的山洪,融合成生命不屈的绝响。我常想,一个人的骨肉中,若是融进了这种豪迈与气场,再大的风雨也就不会畏惧了。 立秋抽穗,处暑开花,锥形伞状花序分枝稠密,向斜伸展,花色有浅紫、淡绿、米黄,多为白色,飞白后的芦花在人们眼里可谓百态千娇,风情万种。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似花非花,似雾非雾,远远的望去,百万亩滩涂柔软成银色的海洋。你可以视它为单纯娴静的女子,可以视它为和蔼贤淑的母亲,也可以视它为敦厚朴质的乡民,无论哪一张脸,都离不开那份原始素洁的本真,凭你怎样坚定的胸膛,只怕也抵不过它柔软飘逸的三钱力量。 “芦苇深花里,渔歌一曲长”。这是秋日,饱满的日光下,茫茫的芦花泛着金色的诱惑,渔舟穿梭在苇荡深处,如梦似幻,或有一曲渔歌长调惊起几只鸥鹭,打破梦一样的安详。此刻,你竟会连自己也不晓得,到底爱它的轻盈,洒脱,还是空茫? 不过,我还是更喜冬日里芦苇的隐忍。冬日的北方,万物躲得那叫个灵巧。旷野沟渠唯一看得到的植物只剩芦苇。深冬的芦苇都脱光了叶子,只剩头顶的一缕缨帽,告诉人们它还在守卫着土地。灰蒙蒙的原野真是家徒四壁的感觉,只有它,壕沟、坝棱子上,像路标似的给人家的感觉,只有它,面对严寒的威逼,还给这残酷的冬天添一丝精致。它倔,好像从地下钻出那天起,就再不能瘫倒下去似的,全身风干了还挺着脖子,好像头上举着的不是疏落的绒穗,而是一份清高与永恒。它隐忍,水泽里生出的骨头,冰封三尺、寒风猎猎,它在等,等下一个春天,等下一个轮回。我常常不忍心头的脆弱,它太像我们的土著,我的父老乡亲。 每个走累的人,都在不停的寻找灵魂的抚慰,精神的寄托,情感的供养。慢慢旅途中,某一天,当推开心头的疲倦,闯入你的心扉、嵌进你的灵肉,或许就是违和的四季,看久的落日或者路边的一簇芦苇。 三 民间关于芦苇有一段古老凄然的爱情故事。 有一片水泽边上住了一家猎户,猎户有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儿,每天女孩都从水泽里提水洗衣做饭。有一年大旱,水泽干涸绝水了,泽底干裂,水草奄奄一息。猎户每天从很远的地方背来水,女孩只留一点点自己用,其余的就倒入水泽,有一棵芦苇深受感动,它暗暗地发誓:我们家族只要有一棵生命存活,定要还整片水泽一片生机。几个月后,干旱过去,芦苇咬紧牙关活了下来,它不忘誓言,修根发芽,一年成撮,两年成片,三年成塘,而且它也深深的爱上了女孩,每天挺直胸膛,伸长脖颈,探着头向着女孩家的方向,盼望女孩的来临,所以也有人说,芦苇,总是向前探着身子生长。可惜,没过多久,女孩出嫁了,嫁到很远的地方,芦苇万分的悲伤失落,但它相信女孩会回来,于是坚定的等待,年年孕育,年年疯长,如果加个期限,那定是一万年。 故事是凄美的,但现实中的芦苇的确年年孕育,年年疯长,只不过,它们没有等来美丽的女孩,等来的却一批批苍鬓虬髯的“刀客”。 提起“刀客”我的脑海不自觉的总会出现武侠小说中那些道骨仙风、入地升天,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可当亲眼见到下塘的“刀客”,什么不食人间烟火,愤世傲俗的大侠形象,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苇塘里的刀客来有影去有踪,它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为了生活讨生计。不过,他们虽没有傲世的风骨,却也深藏的绝技,相比之下,前者或许只是杀富济贫,而后者更具有战胜自然的伟大神力——万亩的野生芦苇在它们的刀镰之下,变得温柔顺从。 比“刀客”更准确的称呼叫“苇客”,比“苇客”更贴切的称呼叫“塘驴子”。 芦苇于10月上旬种子成熟期,10月底以后脱叶,而在11月至来春一月为最佳割苇期。每年的寒冬腊月,辽河三角洲地区成了名副其实的“金三角”地带,东郭、羊圈子、赵圈河、石山种畜场是盘锦境内几个著名的苇场,毗连成金色的海洋。在破马张飞的机械收割没有开进苇塘的时候,这一百二十万亩的芦苇都凭“苇客”的刀镰,码起一垛垛苇捆,装满一车车故事。 “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率土之滨莫为王臣”,古代,哪一块美地肥田都有其该属的地主或田主,而这地主田主绝非是布衣平民。《左转﹒昭公》昭公二十年记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这是说早在春秋时期,山林中的树木,洼地里的芦苇,草野中的柴禾,大海中的盐蛤,都由国家派专人掌管。盘锦域内的大芦荡自有史料记载,自然就未曾放纵于民,清末、伪满、民国时期,成片的苇田基本为官府、内陆地主、民族资本家所有也就合情合理。不管是官府还是个人,芦苇总是要一根一根割下来的,这样,候鸟一样浩浩荡荡的“刀客”受雇而生。即是受雇,盘剥、榨取自然存在,也就注定了刀客们辛苦的命运。 民间有句俗语:“人进苇塘,驴进磨房”。 一句话,刀客们艰辛劳苦的生活入木三分,昭然若揭。或可有另外一层理解:站在苇塘里,你的世界只有芦苇与天空,天空是圆的,苇塘是圆的,无论你站在哪个点上,你都是世界的圆心,苇塘里没有任何参照物,真是有如“瞎驴拉磨”,只等苇塘的芦苇全部伏地,方可转出这个圈。 冬季的东北大地,生硬,寒气逼人,但也抵不住“淘金”的诱惑,刀客们冒着零下二十来度的酷寒,从省内临近地区匆匆赶来,还有更远一点的来自内蒙、吉林、河北、山东等地,为的是在年关到来之前淘得最后一笔金,以蔚抚家中的妻儿老小。他们多是青壮男子,也有刚毅要强的女性。他们一般为夫妻、父子、兄弟、邻居或结伴的乡人,好在收割芦苇赶在冬闲的季节,好搭伴,为的就是在险恶的日子里多一分照应。 早期的割苇人也叫刀工,他们的苇塘生涯及其艰苦。在两个多月的割苇期间,刀工们就吃住在苇塘里。雇主在苇塘里为他们搭建住处,取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塘铺”,其实就是极其简陋的、囤顶的筒子房,土坯堆砌,屋内中间是过道,南北各有一铺大炕,每铺炕上都可以挤下十几个人,也有一铺大炕挤二十几人的,算是有了起居避寒之所。按冬日时令,北方昼短夜长,但塘里没有谁会就着时令,安逸的睡着长长的觉。 饭菜也极其的简单,以高粱米饭、玉米饼子、盐豆子、土豆白菜为主。有时也炖大豆腐。一日三餐有专人做饭,早晚在塘铺里吃,中午,带工的人(组织者)将饭送到工地,没有桌凳,刀工们端着饭碗,找一处背风的苇堆子坐下去,狼吞虎咽一顿饭。 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并不太在意饭菜,能吃饱就行,难捱的还是白天下塘割苇。为了快点赶活,早点回家过年,刀客们两头摸黑地干。看不清就凭感觉和技术往前趟,心一直提着,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或旁人搭上(割伤),啥时候天放亮了,心才松快下来。 老刀客李万肆回忆说,早上四点,老话叫“鬼呲牙”的时候,是冬天一天里最冷的时候,那要是把耳朵搁外边一会,用手一扒拉都能掉下来。咋不愿意也得起身吃饭,然后下塘,一干就一天,晚上五点收工。干起活来,即便脱掉厚衣服也是一身汗,而当直身子歇气时,冷风吹着脊背又透骨的冷。最怕的就是雪后的“抱杆霜”,刀工低头用胳膊搂苇杆的同时,苇穗子上的积雪便纷纷落进脖颈,瞬间化了,刮骨风一吹,全是一道道的蚂蚱口。尤其脚上穿的靰鞡灌进雪去,脚底一会就湿透,那大野地零下二十来度,一会就开始从脚底心拔凉气,一直拔到波棱盖以上,有的正干着活呢,腿就抽筋了,有的收工回到塘铺,脚跟鞋冻在一起了,在苇塘干活没有不得风湿的。 “盘塘”是更苦更累的活,一大捆苇子百十来斤重,根朝上梢朝下,头、肩、背齐用,头顶肩扛到指定的垛场码垛。一个大垛大约有二三百吨,一天下来,肩背就打去一层皮。晚上,下了工,吃过饭,浑身打浑身(不脱衣服)偻头就睡。塘铺的门窗都不严实,冷风从门窗缝嗖嗖的往里灌,他们也浑然不觉。 塘铺里传开一个笑话:一个刀客半夜起来去茅房,迷迷瞪瞪走到对面大铺以为到了茅房,一边解手一边嘟囔,“这黑天瞎火的,满天连个星星都没有,看样子明个要下雪,正好歇歇”。一个睡着的刀客接着说,“哪下雪,这不下雨呢吗?”一骨碌翻个身,脸朝里接着睡。 当然,偶尔也有活轻点的时候,大家挤在塘铺,也有片刻的欢愉。拨亮马灯,插科打诨,有人为白天下塘准备活计,有人围在一起玩纸牌。赶上大雪封塘,也可以蜷在塘铺里改改善,喝点小酒。 刀客在苇塘割苇也是处处充满危险,装车、码垛、绞刹(傻)绳、顺风坡,这些都是危险的劳作。李万肆说他亲眼看到和他一起干活的“二大眼”被刹绳所伤的情景。刹绳也叫爆绳,缆绳,装载重物的大车上通常用它来勒紧货物,稳固车辆平衡,因为又粗又硬,常常套着一根粗棍,人用力绞着棍,绳子就越来越紧,直到绳子吱呀呀叫,货物就被牢牢固定住。二大眼就是帮装苇子的车绞刹绳的。那天,绞绳就差一扣了,一个没注意,绞棍脱手了,飞快的反向旋转,正打在二大眼腰上,“嘭”一声闷响,人被打出好几米远,后来,听说人是活下来了,脾黏连了,再也干不了重活。 苇塘里,雷、火都是致命的武器,刀客们不仅要防火、防雷,倘若在塘里迷了路,生命同样会受到威胁。刀客在苇塘里时有发现“死倒”(尸体),大抵是些捉鱼捞虾、猎禽捕兽的转迷了方向,莽莽苇海,如何定位?只得等刀工放倒了芦苇才见方向。这样看来,刀客的命运远不及一只候鸟活得恣意洒脱。问他们到底有多辛苦,李万肆笑着说:“那日子,就像他们汗湿的衣服,酸涩咸卤。” 九十年代后,苇塘的条件相对好了许多,塘铺盖成了砖瓦结构的“海青房”。割苇人的数量也剧增,最多时可达三至五万人,这时“刀客”被唤为“苇客”,听起来,文雅了许多。“女苇客”的数量递增,多与丈夫同来,几块布帘就能获得一个属于自家的独立空间。生活也相对有了改善,塘铺里都有小卖店,烟酒都可以买到。酬劳也有很大提升,“苇客”依旧不怎么挑吃住,他们唯愿多赚些酬金,早日回家过年。 张牙舞爪的收割机挺进苇塘,意味着“苇客”们将淡出芦苇荡的视线。一台收割机的效率足抵得上三五十刀工的刀镰,如今收割机不能进入的零散苇田还需要苇客人工收割,哪一天,当微型的收割机横空出世,“苇客”,真的如远飞的大雁,不会再回来了。那时,不知望着“苇客”远去的的背影,芦苇会不会有留恋之慨,离开人的苇塘,还有没有故事,离开“苇客”的苇塘,谁还能讲故事? 四 眼前的芦苇,总让我脑子里塞进去很多快乐和浪漫的景象。 苇稞里涡渔网,捉泥鳅,苇塘里抓螃蟹、找鸟蛋、追野鸭,这些浪漫是事,我们那个年代的孩童几乎都干过。 挖芦根当野味,摘苇叶包粽子,割苇杆编席子,拔苇花扎笤帚,似乎芦苇浑身都是宝贝。古人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数千年来,让芦苇今天的社会利用衍生出更多领域:药用、食用、编织、建筑、燃柴、造纸、造丝、造棉、制作家具板材等。在这一众的社会功用中,产生最早、范围最广、实用最强、流传最久、最具传统文化品味的,当属芦苇编织。 在辽河沿岸,在盘锦,苇草编织技艺一直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亦是比较成熟的苇编技艺基地,在这里,若是看到仍保持原始、质朴艺术审美的鞋鞋帽帽和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坛坛篓篓,你就会情不自禁的爱上它们。 这是沿辽河一带,人民为了生存,创造出来的一种手工技艺,盘锦传统手工艺苇草编织技艺里,小亮沟苇编是杰出的代表,延续至今已有余年的历史,它也是移民垦荒文化的代表,彰显了先人们的拓荒精神,蕴含着浓厚的农耕文明以及大辽河的河运商贸文明。几百年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为农耕文明的延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要了解小亮沟苇编技艺还得往先祖的根上刨。 小亮沟是个小村庄的名称,村子很小,像个小小的西瓜子,位于大洼区西安镇东南端,沿河而居。《大洼县志》(第89页)对此地有这样的描述:“这里人烟稀少,芦苇杂草遍地丛生,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占据疆土,从关里大量移民至此”。村里留下一个传说:先人们从关里举家迁移这里时,大大的超出了他们的期待,这里地坦,土沃,水充足,湿地多,繁茂的芦苇荡里各种的禽鸟、小兽随处出没,当时曾留下一句谚语“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如此看先民的生活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其中这刘姓一户人家,就兄弟两人,勤劳能干,每天,捕猎的小禽、小兽吃不完就用苇草围成栅栏圈起来,但它们总能从苇草中挤出来逃走,哥俩于是就将苇草互相挤压着编成网,有了牵拉,小兽就钻不出去了。哥俩接着就把铺炕的苇草也编成网,苇草就不再从炕上滚落,再后来,哥俩试着用刀将芦苇破成瓣,在砸软,编成片片,铺在炕上,这就是农家日用的炕席,也是小亮沟苇编技艺的最初成品。 传说挺美,但似乎又经不住推敲。晏子春秋中讲到“贫士以蒲苇织履为生,压芦苇为席而作”。晏婴乃夷维(今山东高密)人,这说明春秋时苇草编织已在山东盛行,这里的住民大多就是来自山东的移民,怎么是刚刚发明呢?但传说中的刘姓哥俩却是确有其人,且是小亮沟苇编的师祖,或可理解为,故事里刘姓哥俩从关里来此,并把当地的苇编技术也一并带到这里。 刘氏兄弟为代表的苇编织业逐步扩展开来,离不开辽河水运。 小亮沟三面环河,有河湾数处,曾设有下口子“官摆渡”。从田庄台周转、辐射各地的船只大多也经过下口子渡口。每当风高浪急,许多船只纷纷到这里抛锚避险,更有数不清的船只途中到这里停船靠岸,当地百姓便可用当地土产与船主进行简单交易。在当时有限的物资条件下,苇编制品经久耐用,平整美观,织工精细,就极受青睐。以炕席、房笆、茓子、簸箕等实用工具最受受欢迎。随着河运的繁盛,后来关内河北省霸县、大城、文安、静海等地的人陆续来此定居。有精通苇编者将新的技术带来,刘氏苇编把关外草编的巧灵、精细与当地苇编的粗犷实用糅合在一起,造就了其独特的编织技艺。 农耕生产单一,物资匮乏,经济来源少的时代,得天独厚的苇田资源,加上精巧美观的编织技术,小亮沟沿下辽河一带劳动人民有90%以上的人以苇草编织谋生,苇草编成为人们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 那时古镇田庄台一些商家已经抢占了商机,设有苇草编席市,义发合、鸿兴泰、福和、永增长、长兴泰、庆之元、端记分号等席商,每天早市可收买苇席数千片,转手销售辽、吉、黑三省,而织席、卖席最抢手的正是小亮沟沿辽河两岸一带的驾掌寺、王家塘、魏家塘等地的编织手,苇席品种增添了“提尖”、“炕板”、“京庄”、“黑三纹”,另有“四八”等规格小席。苇编事业一度繁荣。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永远离不开文明的翅膀。到了民国年间,小亮沟苇编不只局限苇席、房笆等大件产品,品种上增加了虾苞、鸡蛋篓子、鱼篓、酱斗篷、蒲草鞋、草绳、草帘子”等轻巧实用的家居产品,而且开始瞄准一些花样新颖的苇草编小工艺品。在编织花样上有“三纹、双纹、格纹、斗纹、织字”等。小亮沟苇编开始远近扬名。 “大芦苇,高又长,芦苇荡边编织忙”。这就是30年以前,岁月里的小亮沟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生产队劳资低,挣的工分刚刚够领回口粮。其余的家居用度都靠织席换钱补贴。河边住的人家,没有一家不织席,没有一人(幼童除外)不会织,不,应该说不敢不会织席。 孩子也织席,大人每天给孩子们分任务,如果完不成,那真是“父之一何怒,母之一何苦”,如有贪玩耍滑,轻者一顿不给饭吃,重者挨一顿屁板。因此一家人每天都在一起搞“大生产”。父母终日贪黑起早的忙,父亲穿苇、压苇,母亲踩席头,一下学,或有空闲,孩子们也投入劳动,大孩子织席片,小孩捣席边。这样一天下来,丈二的大席也能赶出来三四领。凑够十领,就由家里壮实的男丁用扁担挑了去集市上去卖。这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极愉快的,尤其孩子,因为有自己的血汗在里面,不只有成就感,也满怀希望,或许这里有自己一只钢笔,一双新鞋。 会苇编的人回忆编织过程是及其享受的一件事,甚至有点浪漫。 单说苇编用的器具就很有趣味,都是百姓根据“实战”自己创造出来的,包括取的名字。⑴拉子⑵三镂穿(chǎn)子⑶四镂穿子⑷五镂穿子⑸磙子⑹尺杆子⑺苇夹子⑻撬子⑼夹了⑽拉席刀,(11)磙杆子。 每个成品看起来大气、简单。但从准备到编织十几道工序十分复杂。 编织前要备料。冬季收割下已成熟的芦苇,捆成直径约0.8米的苇捆。垛成垛,然后进行筛选(也称“投苇子”),然后穿苇子,也叫破苇子,根据芦苇的粗细,用5镂穿子、四镂穿子、三镂穿子、拉子把芦苇破成瓣儿。随后用竹制的苇夹子打掉苇皮,用石制的磙子(也称碌碡)把苇子压熟(压柔韧),按长短投出大苇、二苇、踩脚,剩下的用麻绳也按长短串成链子,分为头篷、二篷、三篷,此道工序可根据苇席的规格,先用木制的尺杆子丈量,根据要编织的作品确定出选用哪种苇子。 编织过程是有口诀的:“踩席头”讲究“压三挑四郞当二”。当苇席向四周扩展时,用苇子连接,也称递糜子。连接好的方正的叫席片。“捣席边”(对席片四周进行圈边)讲究“挑二双,压两双”。织好的席片用水洇湿,然后尺杆子量好,再“包犄角”“打茬子”。最后用铁制的“夹了”,顺着苇席的花纹全面夹一遍,也称密实密实……. 当物质生活充裕到可以让人们自由选择的时候,当苇编已经不再作为人们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苇草编织有那么一段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唯小亮沟人对此情有独钟,年,小亮沟苇草编织技艺申报成功辽宁省为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传承发展,唤起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近年来,芦苇画在盘锦域内也有了广泛发展,用芦苇等材料,通过编、粘等手法,利用高温碳化的原理,制作成画,艺术家就是通过创作苇画,寄托乡情,寄托理想,将生活中的美融于艺术,将艺术融于生活。 一束小小的芦苇,可能会成为精美的工艺品,可能变成家居环保的器物,不惊天但一定惊人,因为这些可能的背后,都有一个执着于梦想的人和故事。 那些旧得发黄的炕席、摆饺子的盖帘、捉泥鳅的鱼篓、茓子围成的粮囤、续上靰鞡草的棉靰鞡,相信,有那么一代人的记忆会永远留在这里。 五 “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的哲学不知唤醒多少人。 在浩渺的大自然中,人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自然之子,人类和他们收割的芦苇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自然的眼里,人和芦苇看起来都是卑微而脆弱的,但无论在怎么恶劣的环境里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人类和芦苇又是迥然不同的。芦苇浑身是宝而自己浑然不知,生生世世反复轮回为自然为人类贡献自己的全部而浑然不觉。 沿海滩涂及内陆盐碱荒地,如果生长了茂密的芦苇,土壤的含盐量就会逐年减少,且时间越长,脱盐效果越显著,据有关调查表明,栽植芦苇10年后,土壤的脱盐效果高达90%以上。芦苇的蒸腾对当地空气湿度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光合作用释放大量氧气可使空气变得更加清新。它的强大的地下根茎系和密集的地上植株,是天然的、功能较强的过滤器。工农业生产生活废水、污水,在芦苇湿地停留五至七天,各种污染物都得到不同降解,水变得清澈,土壤疏松,大大减少了城市污水对江河湖海的污染,因此,芦苇除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直接给人类带来经济利益外,在环境保护、净化污染,别是对保持湿地生态功能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然而芦苇自己全然不知。 人,比之芦苇,有的是思想,有的是思维。 当人类茹毛饮血的祖先点燃第一缕烟火,人类文明升起第一抹曙色。我们的先祖何其明智,他们相信自然,以自然为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那个时期,人与生态系统的矛盾并不突出,人类在给予自然万物充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eizhongcaozia.com/hzczxzjb/62193.html
- 上一篇文章: 家中院子不妨试试种2棵此树,营养丰富
- 下一篇文章: 乐怀居旭峰乡土记忆方言纪实记得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