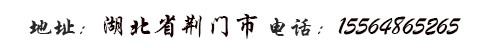民间故事破镜重圆
|
白癜风一对一精细化治疗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80601/6298359.html 老年间,滹沱河南有个单家庄。单家庄村子不大,人口也少,可是村里单身汉多,老光棍,小光棍,兄弟叔伯光棍,数算起来,三口人里就有俩!这一带流传着一句俗话,说是:“有女不嫁单家庄汉。要穿没衣,要吃没饭。”这句顺口溜的俗话传了不知有多少辈了,人们都说,单与单不分,一字二音,所以单家庄的单身汉多,这是犯了地名啦。 单家庄村南口,有个秀才叫单大白。别看单大白身为秀才,也是单身一条没有娶妻,因此人们便称他“穷大秀才”。穷大秀才命运不好,他的爹娘死得早,撇下他和弟弟二白一起过生活,也可以说是大小两条光棍。这一年穷大秀才三十出头,弟弟二白也已十八九岁,二白还没有什么,穷大秀才却是一天到晚三声叹,二白心里明白,哥哥是愁婚姻大事。娶不来媳妇生不下儿,没儿难求孙,要断香烟绝门户啦。思想到这些,二白心里也难受,夜里做梦也发愁。 俗话说,靠山吃山,傍水吃水。二白除了上山砍柴,就是下河捕鱼,靠打柴打鱼卖钱维持家计。穷大秀才除了会读子曰诗云,就是满口“君子固穷”之类的言辞,他不能上山砍柴,也不会下河捕鱼,就留在家里烧烧火,煮煮饭,料理家务。 这一日,二白从滹沱河里打了很多鱼回来,一进院,就听到屋里有个女人在同哥哥讲话。二白心里很觉奇怪,哪来的女人同哥哥拉家常呢?就停住脚步站在院里用心听了起来。听了不大工夫,二白高兴了,原来是媒婆子来他家为哥哥提亲的! 就听媒婆子说:“好我的大秀才先生,你可要掂量掂量哪个轻来哪个重!” 穷大秀才答:“兄弟者,手足也;妻妾者,衣帽也。君子纵是独身,岂可断手足而取衣帽哉!” 媒婆子听不惯了:“你先别转文,人家女方可是吐口了,只要你们兄弟分开过,便嫁你。你家两条汉子,又没父母姐妹,人家过得门来,先要伺候小叔子,谁愿意?” “那就只好作罢。” “作罢?我的大秀才先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穷大秀才在屋里说的这些话,二白全听了去。他心里想,“哥哥的婚事有望了,这真是喜从天上来!人家女方多嫌咱,女方自有女方的道理,可不能因为自己,坏了哥哥的婚烟大事!”二白悄悄地溜出家门,躲到一边去了。 见媒婆子回家去了,二白便追到媒婆子家说:“俺哥哥的亲事,你尽管去说,打明儿起,我就走得远远的,用不着分门立户别锅碗,家业全归俺哥哥!你到俺家就对俺哥哥说,只要俺哥哥能娶嫂子进门,俺当弟弟的就心满意足啦!” 同媒婆子讲定说好,二白回到家来,把打的鱼放到缸里,把卖鱼的钱交给穷大秀才,兄弟二人这才吃晚饭。吃过晚饭,二白抢着刷锅洗碗筷,穷大秀才不让,劝弟弟:“你劳累了一天,快歇着去。” 兄弟二人你争我抢,刷了锅,洗好碗。二白还是站在穷大秀才屋里不去歇息,穷大秀才心疼二白劳苦,就说:“弟弟,哥哥要读书了,你快睡觉去歌歇身子吧。” 二白说:“哥哥,我不累。咱家有了喜事,我欢喜得那能睡着呢!” 穷大秀才很不解,就问:“咱家有什么幸喜事呀?” “哥哥要娶嫂嫂了,这不是咱家的大喜大幸之事么?” 穷大秀才这才明白过来,他连声叹了几口气,接着说:“不娶!不娶!不娶!” 二白体谅哥哥的苦衷,扑通一声双膝竟倒在穷大秀才面前:“哥哥先受小弟一拜!” 穷大秀才慌神了:“弟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快起来!” 二白跪在地上不起,继续说:“自从二老过世,哥哥如同爹娘一般把我抚养成人,哥哥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啊!哥哥要是不答应娶嫂嫂,我就不起来!穷大秀才听了二白的话,心里不由一阵酸楚,两眼不由落下两行泪水,好一阵难过。为了不使二白长跪不起,连声说:“为兄娶也就是!为兄娶也就是!” 二白这才从地上起来,对穷大秀才说:“哥哥今后更要多加保重,天天读书到深夜,可别累坏了身子。” 穷大秀才点着头,叹口气对二白说,“有好多话,为兄真是不便讲呀。” 穷大秀才抱住二白,兄弟俩猫哭了一场!哭过之后,二白劝慰穷大秀才说,“哥哥,不便讲的话,就存肚里不讲不就得了?” 穷大秀才也只能如此,他苦笑着点了一下头。 二白说完,就回到自己屋里去睡了。人躺在炕上,不用说心里没闲着,就是连两只眼都在大睁着!俗话说,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这滋味儿,二白今夜里是体验到了!为了哥哥能娶妻成家,从明天起,他就要离开这个十几年来从未离开过的地方,就要离开相依为命的哥哥,要到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去闯荡,去流浪,去谋生。二白哭着想着,想着哭着,泪水把枕头都湿遍了。不知不觉中,村里传来了鸡叫,三更天了。 二白趁着夜静更深,穷大秀才入睡,起身轻轻地开了门,拿上那张渔网,像个猫儿似地悄悄蹑蹑地出了院门,来到滹沱河边上。他从河旁树木上折了几根大树杈子,用绳子捆绑了一个木筏子,将树杈筏子投入河里,他跳上筏子两只胳膊伸开,乘着筏子顺着汹涌的滹沱河水,自上游顺流漂泊而下。 天渐渐亮了,二白一看,眼前的河道变得开阔多了,无风无浪,两岸是大片大片的沙滩,少有树木,不见人烟。天高地广,水深鱼跃,清静安生,真是个好地方呀,就在这儿落脚谋生吧。二白上了岸,看看离河滩不远处有座河神庙,河神庙的顶子半塌了,墙壁透风,庙里也没了神像。二白心想:“就在这儿安家吧。”他马上动手拾掇起来。 自打安家河神庙之后,二白每天夜里打鱼,白日便拿着打来的鱼到二十多里外的集市上去卖,夜夜如此,天天如此。没过多久,二白不但买来了油米酱醋,添置了锅碗盆勺,连鞋袜裤褂也全换成新的了,铺盖被褥也全有了。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生活,虽说是安闲自在,可是一想起家里,想到哥哥穷大秀才,二白就掉泪。哥哥现在怎么样了呢?嫂嫂娶过门了没有?自己离家出走快一百天了,一点儿音讯全没有,这河神庙距离老家单家庄太远太远了,那天他在集市上打听,这附近的人们都不知道上游有个单家庄。自己在滹沱河里漂流了整整半宿的工夫呀! 离开单家庄的一百天头上,二白正在河边散网打鱼,天近中午,忽然来了狂风暴雨,狂风刮得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暴雨浇的人睁不开双眼;天上雷鸣电闪,河里被浪滚翻,二白只好急忙忙收起渔网,跑回河神庙来。他回到河神庙,就听得天空里连声地响起霹雷,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紧,由远到近,响到这河神庙前来! 霹雷声使人胆战心惊,震得河神庙摇晃掉土,二白长了这么大,头一回听到这么响的霹雷。忽见从淹没的大雨中跌跌撞撞地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浑身泥水披头散发,丢魂落魄般地一头扑在二白身上,便昏过去了。 二白忙弯下身去搀扶这人时,只听得“咔嚓嚓”又是一声霹雷,震得二白两个耳朵都变聋了,过了好一会儿,外边风声弱了,雨变小了,雷声停了。待到他惊魂甫定,趴在地上的那个人也站立了起来。二白定睛一看,差一点儿惊叫起来:这人是个大姑娘,年岁同二白相仿,生得眉清目秀,不胖不瘦好体格,不高不矮好身段。二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倒是那姑娘裣衽施礼先开了口:“多谢大哥护救之恩。” 礼尚往来,二白只得还了礼问道:“大姐一个人从哪里来,还要到哪里去?” 姑娘说:“我随家父逃难来到这里,人地两生,没有活儿干,便和爹爹在这滹沱河上打鱼糊口。又因为新来乍到,水土欺生,老爹爹因不服水土染病身亡。撂下我一个女孩儿家,无处投靠,我便投河自尽,谁知大限未到,河水把我冲到河滩上来。我刚还过阳来,又遇雷雨交加,我无处躲避,这才逃到你这河神庙里来了。要不是有大哥护救,在这河神庙里避难。我不被暴雨淋杀冷杀,也被霹雷劈杀了!”讲到这里,姑娘又施一礼道谢。 二白听了姑娘的这一席话,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就说:“大姐为何不回家去呢?你家住哪里?” 姑娘说:“回家?我家住塞北苏武泡子,山高路长,一个女孩儿家,又如何办得到呢?” 远隔千里,说的是呵,千里迢迢,举目茫茫,一个年轻女子,无钱无势无车马,要回塞北老家,千山万水路遥遥,这真比登天还难! 二白叹口气说:“那你今后可怎么办呢?” 这里二白一句问话刚出口,引得姑娘哽哽咽咽,哭哭啼啼起来:“真是呀,无家可归,举目无亲,活着不如死了的好呀!”说着,又冲着滹沱河跑去,要投河寻死。 二白慌了,急步上前,拽住了姑娘:“大姐,使不得!” 姑娘回转身来,逼问一句:“大哥你要收留我,奴家就不去死了。” 二白作难了,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的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姑娘急了,挣扎着说:“大哥要不肯收留我,就让奴家去死吧!” 这时二白把牙一咬,用力说:“大姐,宁可让人说长道短,我怎能见死不救?我收留你!” 姑娘忙深施一礼,破涕为笑:“大哥肯收留我,奴家更愿意伺候大哥一辈子!” 二白这时才明白过来,姑娘要他吐口说的“收留”二字,是嫁给他,成就夫妻的意思。二白心想:一个小小的河神庙,摆不下两张床,也没有里外间,要不是两口子,根本没法子住。看来天合人意,两人注定要配夫妻! 风停了,雨住了。雨过天晴,河水澄澄清,日月更光明!当天夜里,二白和姑娘撮土为炉,插草当香,对着满天星月,拜天拜地拜父母,成就了夫妻。 二白对姑娘说:“人家成亲要喝合卺酒,咱没有酒就喝白水当酒吧!”说着,他从水瓮里舀出一瓢水,递给妻子喝。 姑娘说:“你先喝,夫唱妇随呀。” “好!我来先喝!” 二白仰起脖子端起瓢,咕咚咚,一连几口喝下去,他眨巴眨巴眼睛,直吧咂嘴唇:“这水怎么真像酒了呢?” 姑娘笑着说:“俺来喝一口尝尝!”她接过瓢来,也咕噜噜喝进好几口,“你在逗人呀,这瓢里明明盛的是酒呀,这香喷喷又绵又醉的好酒是从哪儿打来的?” 夫妻俩说说笑笑的一个劲儿地乐!二白对妻子说:“不用媒人撮合,咱俩做了夫妻,嘿嘿,真稀罕,你和我谁也还不知道谁的姓和名呢!” 姑娘说:“你说得可不对,你不知道俺的名和姓,俺可知道你的姓和名!你叫单二白。” 二白心里奇怪了:“是谁告诉你俺叫单二白的?” 姑娘只是笑着说:“除了你,还能有谁?刚说出嘴的话儿就忘死了,真是没记性!” 二白也认可了,一定是自己没留心说漏了嘴,要不妻子哪会知道呢?他问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 姑娘说:“俺姓古,叫小月。” “‘古小月’?多么好听的名字呀!” 小月说:“名字好听难听有什么要紧?名字又不能当吃喝,当衣穿,当钱花!咱家这样穷,咱两口子要勤勤恳恳置家业,节节省省过日子,拿着黑夜当白天;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呀!” 听了小月的话,二白满口称赞:“你说的好!从明天起,咱夫妻俩就打对锣鼓干起来!” 小月说:“等什么明天?今夜里咱就到滹沱河里打鱼去!” “好!” 月亮白光光,照得大地如同铺了一层霜。小两口一同来到滹沱河边,二白撒网,小月提个篓子捡鱼。 可是,一网一网打下去,提网,收网,网网空!二白说:“今夜这是怎么啦?一个鱼儿也不上网,真气人!” 小月说:“看我的!”说着从二白手里接过渔网来。 二白说:“你还会撒网?” “看你,俺不是对你说过吗?又没记性了!”小月说罢。双手一扬,撒得那渔网圆圆的像支起的伞!网“唰”的一声落入河水里,小月便收起网来。那种熟练劲儿,连二白看了也叫绝! 小月收网,一步一步,越拉网越沉;等到网一露出水面,网里的大鱼小鱼,活蹦乱跳,大大小小,足有二十多条!二白可乐了,他一边捡着一边嚷“你还真有两下子!” 小月撒网,一网比一网捕得多二白用篓子运鱼回家三、四趟!捕的鱼足有两三百斤! 从此,小两口夜里撒网捕鱼,白天上集卖鱼,一日一个小秋,一年下来,攒下了不少银钱。银钱多了,小月对丈夫说,“咱盖房吧,过去穷,住这破河神庙安身凑合着过,如今富了,应该置处宅院了。” 二白摇头:“不盖房。” 小月又说,“那就买地置田产吧,有了自己的田地,再不用水里来水里去,你我夫妻男耕女织,也像个过日子的样儿。” 二白又摇头:“不买地。” 小月问二白:“郎君,积攒了这么多银钱不置家业不盖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 二白对妻子说:“小月,你不是说要‘夫唱妇随’那就听我的话吧。” 小月不想同丈夫拌嘴,就说,“好,就依你。” 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小两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攒的银钱更多了。小月又对丈夫说:“郎君,我看咱还是快置家业吧,攒下这样多的银钱不派用场,咱两人不成了守财奴了吗?” 二白说,“守财奴就守财奴!” 小月听丈夫话里有气,就解劝,“郎君,为妻说的不过是玩笑话,值不得动气呀。钱财再多,积攒存放在一处也不会生下小的来呀!” 二白说,“这我知道。你还不会生呢,又何况钱财这些死物呢?” 一句话,把小月说得哭了起来。小月收拾了一下自己穿的衣物,包了一个小包袱,挟在胳膊腋下就往外走。 二白慌了:“你到哪儿去呀?” “回娘家!” 二白一见小月动了真气,也知道自己的那句话戳疼了小月的心,忙拦住妻子,直劲赔礼说好话:“我跟你说句玩笑话,你怎么认起真来了?你一走,我可活不下去了!” 小月一边哭一边数说:“你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为妻同你日夜相伴,捕鱼上市,前后忙活,一天到晚,含辛茹苦;一年到头,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实指望成家立户,也好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谁知道你听不得良言相劝,反对为妻恶语相讥,真叫人眼里淌泪,心里淌血......” 二白一边劝慰妻子,一边披露心迹:“你哪里晓得我的心事呀!” 小月问:“什么心事,难道还要隐瞒为妻不成?” 二白说:“不是我隐瞒于你,我想多积攒下些钱财,日后回归故里。” 小月听得丈夫这样说,就接口追问:“你说的是要回到单家庄老家去吗?” “是呀,落叶归根,人回故土。” 小月摇摇头说:“郎君,不可,万万不可!这地方天高地阔,水绿山青,既没有虎豹豺狼,又没有恶霸强盗,白天丽阳高照,夜间月明星灿,真可以说得上是世外桃源!我们夫妻在这里建家立业,安心度日,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岂不胜似神仙!” 二白听不进妻子的话,小月也说不转二白的心。小月赌气说,“郎君坚持要回单家庄老家,那么,俺更思念远在塞外的亲人!你回老家,我回娘家,明夫妻俩就各奔前程吧。” 到底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爱”,气话好说,气事难做。小两口和睦美满,谁又能割舍得谁呢? 不知不觉中又要过年了!二白自打离开老家单家庄出走,屈指算来已有三个年头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一奶同胞的哥哥穷大秀才!打探不到哥哥的音讯,听不到家里的消息,二白一想起老家,一想到哥哥,就揪心般地难受。要不是有小月朝夕相伴,他想家想哥哥怕要想疯了。如今,一提老家,小月就要回娘家,他既舍不得夫妻分手各奔前程,又舍不得放弃回归老家的心愿和念头,这可真是左右为难呀。二白心里盘算着,饭吃不香,觉睡不稳,心事成了心病,到后来连茶饭也不咽了。眼看离年关越来越近了,二白病倒在了炕上,身子也消瘦了下去。 文夫一病,小月心急火烧,她日夜守护在二白跟前,千遍万遍地问他:“郎君,你这是怎么啦?到底哪儿不舒服?” 二白躺在坑上摇摇头,一句话儿也不说。小月急得禁不住哭了起来。听到小月在哭,二白眼里也滚出了泪珠珠。他有气无力地说:“小月,我想家,想哥哥……可,可又舍不得你呀!” 小月看着丈夫,她觉得二白是那样可怜,有心不同他一块回归单家庄,那样做,岂不等于要了丈夫的命?罢罢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夫唱妇随了。想到这里,小月把牙一咬,下了决心:“郎君不要再为难了等你身体好了,一过年,正月里咱夫妻一同返回单家庄吧。” 二白听得妻子这样说,立刻抓住小月的手问道:“这话可当真?” “为妻什么时候同你讲过假话?” 二白见小月同意和他一起返归故里,病就好了大半。他对小月说:“迟也是回去,早也是回去,我看还是年前回老家的好,这破河神庙我是一天也不愿待了。” 小月暗自叹了口气,又依从了丈夫。 二白见小月同意自己的主张,病很快就全好了,他到得集市上,花钱买来了两匹马,腊月十九这天大早起来,夫妻俩收拾停当,带上积攒的钱财,离开河神庙,顺着河岸,打马向西,直奔滹沱河上游去了。 走一程,小月就停住马回头看看河神庙。二白问她:“小月,你在看什么呀?” “河神庙。破家也难舍呀,这是我大难不死和咱俩成亲的地方呀,俺心里真舍不得离开这儿呀。” 二白听妻子这样说,心里也觉不是个滋味,也伤感。不管怎么说,老家、新家都是家,穷家、破家也是家;没有这河神庙存身居住,哪能有今天呀! 两口子晓行夜宿,走了整整五天,腊月二十三的晚上,这才赶回单家庄来了。 一进村,二白就听乡亲们说了,他哥哥穷大秀才早已为他娶了嫂嫂,如今已为他生下一个侄儿。嫂子眼下又已身怀六甲,明春又要开怀。二白听了,心里十分高兴,他忙跳上马背,兴冲冲地带着小月朝自家奔去。 三年前二白出走的那天,哥哥穷大秀才起床以后还以为弟弟又是早早下河张网捕鱼去了,便没有在意,直到二白没来家吃早饭,穷大秀才还蒙在鼓里。中午饭二白没来吃,晚饭也不见二白回家来,穷大秀才这才慌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 正当穷大秀才坐卧不安,里走外转的工夫,媒婆子来了,把二白的话如实全告诉了他。穷大秀才听了,深深为弟弟的真诚所感染了,不娶妻成家,又怎么对得起弟弟二白呀,可不能辜负了弟弟的一片苦心!他抹去了满眶的泪水,当即向媒婆子答应了亲事,择了个日子,把妻子娶过门来。 穷大秀才娶的媳妇姓乔,村里人都称她乔氏。这乔氏长得模样非常丑陋,塌鼻子凹眼窝,满脸都是玉黍粒样的大麻子。模样丑陋倒还没什么,乔氏,心胸狭窄,小心眼子多,就为这,穷大秀才经常同妻子乔氏拌嘴吵架。为了不辜负弟弟的情谊,且乔氏又生下一子,更没法子休她了,所以穷大秀才只得同妻子凑凑合合度时光。 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乔氏买来了祭灶的糖瓜,穷大秀才同乔氏一起烧香上供,送灶王爷升天。乔氏祷告说:“灶王爷,你老可要上天言好事,回空降吉祥呀!” 穷大秀才却祈祷说:“我弟弟二白外出三年有余,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求神灵保佑,让他早归故土,也好阖家团圆!” 这里穷大秀才的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二白在喊:“哥哥!嫂嫂!小弟我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穷大秀才听到二白的呼喊,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他急忙忙同乔氏出门一看,果然是弟弟回来了!他激动万分,一个箭步扑上前去抱住二白,兄弟俩都说不出话来,像是变哑巴了一般!许久许久之后,二白这才先开了口:“哥哥,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离了!” “对!对!”穷大秀才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二白,说:“弟弟,你让为兄想得好苦呀!这几年中,你受苦了,这全是为兄不好啊。” 二白说:“哥哥说的哪里话,我们一家添人进口,大喜大幸,值得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呢。小月,快来拜见哥哥和嫂嫂!” 小月走近前来向穷大秀才和乔氏问候。穷大秀才刚才只顾同二白叙述离别苦和思念情,竟完全没有注意到弟弟已经娶妻成家,更没有注意到这如花似玉,落落大方的弟媳妇。乔氏见小月人才出众,相貌端庄,对她一口一个嫂嫂地叫,也显得分外欢喜。二白两口子先是把马拴好,又把钱财卸了下来,一家人这才进到屋里,连吃晚饭带叙家常,直到鸡叫过头遍这才睡下了。 也许是在路上着了风寒,半夜里二白闹起肚子来,他起床去茅厕解手,要经过哥嫂窗前。哥嫂屋里虽说黑着灯,可是哥嫂还没入睡,两个人仍在说话呢。只听穷大秀才说:“弟弟这一回来,欢喜得我连觉都睡不着了。” 又听得嫂子乔氏说:“我同你正相反,他们一回来,愁得我睡不着了。” 嫂嫂这话是什么意思?二白不由止住了脚步,继续听下去,只听到穷大秀才问:“你怎能这样说话?” “俺这么说有什么错?人稠屋少,住不开了呀。” “屋小房少,等以后再盖就是了。” 乔氏鼻子哼了一声,说:“盖?你吃了灯草,说得轻巧!你家本来就穷得墙透风,老二一回来,家业先劈去一半,明年俺再生个孩子,操心作难的事情都在后头呢!” 二白听到这里,心里一打沉:嫂嫂说的都是实情呀!自己是向媒婆子声明不要家业的,说过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可不能往回收呀。二白解过手回到屋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小月被丈夫吵醒了,问他:“夜静更深的,有什么事?” “你看咱这屋小房少,住不开,得买地基盖新房呀。” 小月又好气又好笑:“这个还用说吗?等过了年咱就操持着盖,盖房买地的事儿由我办,你就把心放到肚里吧。” 第二天,单家庄的人们都听说二白回家来了,还领回个天仙般的漂亮媳妇,都跑来看。单家庄有个风俗习惯:谁家娶了新媳妇,村里人都请新媳妇去“赴席”,叫作“认乡亲”。小月虽不算是新媳妇了,可是从外边新回到老家,四邻八家仍要按新娶的媳妇来看待,从年前到正月里,小月每天都要到各家去赴席认乡亲。 刚刚出了正月,小两口就商量买地造屋的事。小月坚持买了离单家庄半里地外的三十亩土地。 二白问她:“为什么偏要买这离村远的土地?” 小月说:“图个清静安生。” “光为图清静,下地干活白跑多少冤枉腿,从春种到秋收,又要走多少冤枉路?” 小月笑了笑:“不跑冤枉腿,也不用走冤枉路。一就两使,就在这三十亩地里盖座宅院,下地回家两方便!” 要盖房了,小月对丈夫说:“盖房的事儿你不要操心,都由我来管好了。” 买砖,买瓦,买木料,跑前跑后,都是由小月一个人来操办。砖买得不多,瓦买得不多,木料买得也不多。二白问妻子:“小月,这砖瓦木料够盖一处四合院的吗?” 小月答:“够用,绰绰有余,我算计着连垒鸡楼的都有了。” 二白虽说不认为妻子是在开玩笑,可心里却觉得备料少,怕不够用,实实在在犯疑惑。他又问:“咱这宅院什么时候盖呀?” 小月说:“盖房的把式说要打夜作,今晚上就开始盖!” 到了夜里,小月一个人去监工盖房,二白和哥嫂留在家里睡觉。果然,村里人都听到砌砖垒墙的一片瓦刀响,和提泥扔砖的呼叫声。第二天,二白和村里人们赶去一看,呀!巍巍挺拔,周周正正的一所新宅院,已经垒了一半多了。更教二白吃惊的是,买来的那垛砖,那堆瓦,那堆木料,都好像没有动用似的,仍旧是那么多,真真是怪呀怪! 第二天夜里,又是乒乓叮当地响了一整宿。到得天亮了,人们站在村头远远望去,只见一处新宅院盖成了。 一连两天,人们都觉得惊奇。到了第三天晚上,有好事的人跑到房顶上去朝二白家盖房的地方一看,只见那儿灯火通明,和泥的、抹墙的、安门的、上窗的,也不知有多少人正在装修新房哩。 新宅院盖好了,果然还垒了个鸡楼,砖瓦木料不缺也不多,正好。二白和小月搬到了新家去住,乡亲们都来庆贺小两口乔迁之喜。为了答谢乡亲们,小月请乔氏来帮忙准备宴席,她自已骑上马赶集操办割肉买酒去了。 一座大宅院没有旁人在场,乔氏对二白说:“兄弟,当嫂子的有句话也没问过你,今个就咱叔嫂俩,弟妹上集了,我想问问你,不知这话当讲不当讲?” 二白听了乔氏的话,就说:“嫂子,看你说的,自家兄弟,有什么可隐瞒的?您有话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有什么不好讲的,又何必吞吞吐吐地不直话直说呢?” 乔氏说:“嫂子总觉得,弟妹小月可能不是个人……” 二白一听这话,不由身上一激灵:“嫂子,你说什么?” 乔氏说:“我估摸,她反正不是人。” 二白睁大了两眼急急问:“小月不是人,又是个什么呢?” “嫂子说出来,你害怕不害怕?” “我不害怕。” “你相信不相信?” “这要看说得有道理没道理,有根据没根据。” 乔氏说:“嫂子决不会凭空瞎说乱猜疑。我想,弟妹不是鬼,就是怪;不是妖,就是精!” 二白连连摇头直摆双手:“小月怎么会是鬼怪妖精呢?俺可不信!” 乔氏说:“你俩怎么认识的,怎么成的亲,嫂子一概不清楚,你可以好生回忆想一想。嫂子犯疑的是,你们成亲几年了,她怎么直到如今还不开怀?如若她真是个女人,不是精怪,早该生儿育女了,这是一。” 二白觉得乔氏说的话不无道理,就问:“那二呢?嫂子快往下说。” 乔氏说:“从古至今,谁见过盖房打夜作的?你们新来乍到,为什么偏要到大旷野地里盖这宅院?打夜作,她一个女人,人生地生,又是打哪儿请来的盖房班儿?这些,不值得好生思想思想吗?” 二白听完乔氏的这一席问话,联想到买的那点儿砖瓦木料,又怎么能盖成这么一座大宅院?他的心里也着实犯疑了。人不提醒不知呀,不怨嫂子犯疑,也确确实实值得思索。二白正要同乔氏商量弄清妻子真面目的办法,小月赶集回来了,把叔嫂二人的话题搅断了。 小月从马背上的褡裢里取下买来的酒肉,鸡鱼,对乔氏说:“咱先蒸馒头,后做菜,行不行?” “行。” 妯娌俩一齐动手,和面的和面,生火的生火。小月和好面,乔氏生好火,两人揉起馒头来。 乔氏说:“弟妹,晚上要来好多人,你和的面少不?” “嫂子,不少。” 小月和的面只够蒸一笼馒头,乔氏又问:“只蒸一笼馒头够吃吗?” “嫂子,够吃。” 乔氏不好再说什么了。蒸好了馒头,妯娌俩又烧起“打蒸锅”的鸡鱼肉来。两人一共装了四凉四热八个碟,大荤假素十个碗。乔氏眉头一皱,说:“他婶,这只够一个席面的呀?” “嫂子,没事儿。有一个席面的就有十个席面的。” 傍晚,乡亲们来了,坐了满满三桌。乔氏暗暗叫糟糕,一笼馒头哪够吃?一个席面又怎么分开供三桌?这回丢人现眼是不可避免的了。 小月满面笑容地应酬着前来祝贺的众乡亲,她对乔氏说:“嫂子,您上酒来我上菜!” 乔氏往三个桌上分别上酒。看了头一桌还没什么,四凉四热八个碟儿,再看第二桌,哎呀!也是同样的四凉四热八个碟儿! 再瞅瞅第三桌上,同前两桌碟儿相同,一模一样!菜相同,八个碟儿变成二十四个碟儿了! 乡亲们把酒喝足了,小月又笑嘻嘻地喊:“嫂子,我上馒头你上蒸碗吧。” 她娌俩又忙活开了。乔氏从锅里端出一碗鱼上了,回来一看,锅里又补上了一碗!端不端不见缺,上不上不显少,莫非是财神爷跟来了?乔氏嘴上不说,那心里可就嘀咕起来了。 小两口和乔氏陪同众乡亲吃饱喝足,人们陆陆续续散去回村里了。二白因为心里生疑,喝闷酒喝多了,他都有些醉了,一走一晃地倒到炕上,直勾勾地盯着小月看起来。 小月觉得丈夫有些异样,就问:“郎君,你直看奴家做什么?” 二白醉了酒,说起话来可就不讲分寸深浅了,他问:“小月,你,你说实话,你到底是人是鬼还是妖精?” 小月听了二白的话,脸一下变白了,她怔怔地望着二白:“你……你说的是醉话,还是疯话?” “不是醉话,也不是疯话,是是实话。” “这么说,你是成心要刨根问底儿?” “对……对了。” 小月眼里急得要着火了,她噙着泪花,问丈夫:“郎君,你我夫妻一起过了三四年了,这三四年来,我们同甘共苦。朝夕相伴,生死相依,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为妻难道还要害你不成?如要害你,又何必等到今天!” 二白说:“既是这样,那你就把实底儿交给我,你到底是人是鬼还是妖怪?” 小月说:“并非为妻有意隐瞒于你,我们夫妻数年如一日,相亲相爱,相安无事,你何必非要穷追细访断缘分呢?” 这时的二白因为酒喝多了,酒力助着他,说起话来可就不掂量个轻重大小了,他对妻子说;“小月,打从河神庙成亲时,我对你就有疑心:为什么天上打霹雷时你倒在地上?为什么舀的那瓢水变成了酒?为什么你一网打上那么多鱼?为什么一提生孩子你就哭着要回娘家?为什么盖房你要打夜作,买了不多的料却盖成了这么座大宅院?平常人能办得到吗?要不是妖魔鬼怪能使法术,谁人又有这等本领!” 小月听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既然郎君早就对为妻有疑心,我也就更应当自爱了。我只告诉你一句;我小月既不是鬼怪,也不是妖魔。我再追问你一句:要我告诉你真情实话也可以,你怕不怕断了夫妻缘分?” 二白还以为小月是故意骗他,便说:“我不怕断缘分,只要你能把真情、真面目告诉我!” 小月听了,两眼刷地流下了泪水,她长叹一声;“天意如此,命该如此,我小月枉有一厢深情厚意了!” 她看看二白,二白也正望着她。小月说:“我不是鬼怪妖魔,我是修炼得道的狐仙。我有五百年道行。河神庙成亲那年,是我的大劫之年,也是我修炼中的最后一关。父亲要我远离故土,躲灾避难。那雷公电母,狠命追赶,我差一点被他们雷劈了;那天在河神庙你弯身一护,我躲过了灾难,这才得脱在天之劫。我感念你的恩德,这才以身相托,实指望永结秦晋之好,白头偕老,没料到中途分手,天各南北!好在你回归故土,也有了这处宅院,今后再娶一房妻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吧,也算我小月对得起你!只可惜我肚中五个月的孩子,还没出世落草,却要变成缺爹少娘的孤儿了!你又怎么懂得,仙体和人体大不同,不过三载,难得受孕怀胎呵。”讲到这里,小月泪如雨下。 这时节,二白的酒也醒了一大半,他拉住小月的手:“小月,都怪我不好,你可千万别走啊!” 小月抹着眼泪,摇了摇头:“你我夫妻缘分已尽了!人间有人间律条,仙家有仙家规矩。你逼我吐露真情,早已犯了仙家大忌,留下来会毁了我,还要连累你一家,毁了你!事已至此,就只能返归族里,我也不愿丢了五百年道行,修不成正果,前功尽弃。我小月再三问你,你不怕断缘分、丢情谊,你讲的话由不得我,我们仙家的事也由不得你!你不是要看我的真面目吗?好,你看吧!”说着,小月倒地一滚,只见屋中出现了一条火狐。 那火狐望了望二白,说声:“别了!”就听“哧”的一声,一道火光飞出屋外,直朝东北方向而去。 这里小月走了,走得无影无踪了一所大宅院就只二白一个人了,他感到孤单单,十分空虚,十分冷清,十分懊悔,十分丧气!思想起几年来的夫妻恩爱,比山重,比海深,多少情意!二白简直要变疯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村里,去找哥哥嫂嫂了。 穷大秀才听得说小月走了,问明了原委,他直气得身心打颤。穷大秀才走近乔氏,啪啪啪!一连三巴掌,打了乔氏一串耳光,“都是你这臭婆娘多嘴多舌,拆散了一对好鸳鸯!” 穷大秀才又扭过头来,训斥二白说:“小月待你真心实意,你犯的什么猜疑!异类与人成婚,更是一往情深,忠贞不二。你看那《白蛇传》里的白蛇,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何苦逼问她的身世?” 二白更是悔恨万分,说:“哥哥,小月一走,我没法子再活下去了呀,她舍得下我,我可舍不下她呀。” 乔氏说:“兄弟甭难受,我托人给你说个更好的媳妇来。” 二白说:“除了小月,就是那仙女下凡我也不要!” 从此,二白思念小月心切,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半个月过去,他竟然病倒在炕上了。请医吃药也不见好,求神拜佛也不顶用,眼见得二白身体消瘦,十指骨细如柴了,直急得穷大秀才里走外转,无计可施。 这一天,二白把哥哥叫到炕前,对穷大秀才说:“哥哥,我要是死了,入殓时让我的身子趴着,开坟时要头向东北。” 穷大秀才问:“这是为什么呢?” 二白气息奄奄地说:“小月的家住在东北,我的心在想着她,人死了,身子也还要向着她,她忘了我,我可忘不了她呀。” 穷大秀才听了,说:“弟弟,你既然知道她家住在东北,为什么不去找她?她过去对你说过吗,她家住的地方叫什么?” 一句话提醒了二白:“哥哥,小月曾说,她家住塞北苏武泡子。” 穷大秀才高兴了:“弟弟,有这地名,就一定有这地方;到得这地方,还愁找不到小月吗?” 二白更是喜上心头,哥哥说的话有道理,对,是应当前去寻找小月呀,光躺在炕上苦思冥想,又怎么能见到小月呀。心里的疙瘩一解开,二白的病很快地就好了。他备足了银两,骑马上路,直朝东北方向奔去。 离开河北老家,二白寻找小月心急如火,因此他日夜马不停蹄地赶路。这样下去,三天五天还可将就,日子一长,那马跑乏了,累病了,任凭二白如何吆喝,如何用鞭子抽打,那病马再也走不动了,一头栽了下去,倒地上死了。 路途遥远,没了坐骑,又如何赶路?没办法,二白只好又买了一匹马,他再也不敢日夜兼程地扬鞭僵马了,只得晓行夜宿,生怕再把马累病了。 越朝东北走,城镇越少,村庄越稀,天气越冷。二白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可是问了成百上千的人,无论年长的还是年少的,谁也不知道有苏武泡子这个地方。 这天晚上,二白宿进了路旁一家小店。他同店家:“请问苏武泡子在什么地方,不知你听说过这个地名没有?” 店家告诉他:“客官你算问巧了,这里除了我,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苏武泡子在蒙古那里,离我们这里怕有上千里路程呢。我老爷爷在世的时候,常对我讲起他年轻的时候曾随白大将军征北,到过那儿。苏武泡子东边不远,有大小两座红山,那红山原本是一座。白大将军用大炮将这红山轰成了两座,西边的叫大红山,东边的叫小红山。怎么,客官要到那儿去吗?” 二白点点头说:“是的。我要去苏武泡子找人。” 店家吃惊地一摸脖颈子:“什么?寻人?那儿哪有人烟!听我老爷爷说,当年他随白大将军征北经过那里,不但山林草莽中有狼虫虎豹伤人,还有妖魔鬼怪害命。你单人独马,这不是去找死吗?不是俺说话难听,何处的黄土不理人?要寻死,不如就近找个地方,还能落个囫囵尸壳,到了那儿,连根骨头也留不下来呀!劝你还是别去的好!” 二白不好再往下说什么,他找小月的心事又怎能同店家明说细讲呢?他想:离家上路已经一个半月了,好不容易总算打听到苏武泡子在哪里了,豁出去了,就是九死一生,粉身碎骨,我也要去!找不到小月,我死了也合不上眼! 第二天,二白辞别了店家,备足了干粮,继续赶路。一出塞,但见荒草成窝,西风怒号,满眼不见人烟,天地间一片荒凉。说是赶路,可又哪儿看得到路!二白只抱定一个信念:朝东北方向走! 走来走去,越往前走,情况越发不妙:先是干粮快吃光了,再就是有时走了一天,连口水都找不到喝;到得夜里,无处存身,二白只好同马蜷缩在一起,一夜下来,几乎冻个半死……这步履的艰难,生活的困苦,实在是比赴汤蹈火还要受熬煎,受折磨呵! 终于,有一天二白饿得眼里冒金星,心里发慌,一个跟头从马上栽下来,昏迷过去了。直到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刻,他才苏醒了过来。二白侧侧晃晃地站起身,扶着那匹日夜相伴的马,对它说:“马呀马,你逃条活命去吧,这儿好歹还有你能吃的草,我单二白已经五天五夜水米没沾牙了,现在饥渴得连说这几句话都没有力气了,我怕是活不下去了,你就自己找条活路去吧。” 听二白说完这些话,那马儿好像真通人性,听得懂二白的意思,咴咴叫着点了点头,然后自管朝前跑去了。 连马儿也跑走了,二白躺在大草地上,远远看去,他就像个死人似的,孤零零的一动不动,除了眉毛还活动,连手脚也如同僵死了一般。黄昏过后,黑夜来临,塞北大草地黑茫茫阴森森,多疹人呀!二白仰面朝天。小声地自言自语着:“小月呀小月,为了找到你,我吃遍天下苦,受尽人间罪也没什么要紧,搭上这条命也值得;谁让我胡乱猜疑,又听不进你的话断了夫妻情分,伤了你的心呢?千错万错都是我一时的错,思索起来,我好后悔呀!我如今是快死的人了,见不到你一面,我死了也不松心呀!” 二白叨念着,不知不觉睡着了。 小月来了。二白见到了小月,欢喜得一蹦就蹿了起来!他扑向小月:“小月,你让我想得好苦!也让我找得好苦!” “我们早已断了夫妻缘分,你是你,我归我,两不相干,你想我做什么?又找我做什么?” 二白急得眼角都要裂开流血了:“小月,你就这么无情无义了吗?” 小月冷笑一声:“无情无义,先说不惜同俺断缘分的是你呀!” “那天我喝酒喝多了,酒后失言,小月,你就不能担待了?” 小月仍旧冷冷一笑:“快回去吧,再不走,当心老狼吃了你!” 二白还要说什么,小月理也不理,转身就走。二白出于着急,忙去拽小月,不料一阵冷风吹来,他打了个激灵,一下子坐了起来,揉揉双眼一看,哎呀,自己这不是在做梦吗?还躺在昨晚那地方,又哪里有小月的影子呀!二白又一看,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虽说是做了一个梦,可是梦里见到了小月,二白又熟睡了一宿,他立刻觉得身上来了劲,站起身来继续朝着东北走。他想的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到苏武泡子找小月! 正慢慢走着,二白忽然觉得有人趴到他身上来了。他正说要掉头回身看看是谁,忽然一眼瞥见那搭在他双肩上的两只毛茸茸的爪子!二白心里惊叫了一声:“老狼!”他听人说过,狼趴在人肩头上,就是为了乘人不备一回头,来咬断人的咽喉的,自己千万不能回头转身呀,一转身可就没命了!可是光这么站着不动,又怎么除掉老狼呢?正在二白没法子可想的时候,从天空里猛然飞来一只苍鹰,这苍鹰飞得疾,看得准,只听得“叭!叭!”两声响,那铁钩子一样的嘴,把老狼的一对眼珠子锛了去!狼的眼被苍鹰锛瞎了,直疼得它打着磨磨转地嗥叫起来。二白也不知从哪来的那么一股劲,一蹿骑到老狼身上,抡着的拳头像榔头,一阵猛打,把只老狼给活活打死了!打死了老狼二白还不解气,从一边捡来个石头片子当刀,剥了老狼的皮,生喝狼血解渴,又生嚼狼肉充饥。 喝了狼血,吃了狼肉,二白用狼皮把吃剩的狼肉一包裹,扛在肩上继续赶路。这狼皮,夜里睡觉当被褥,剩下的狼肉作干粮,好不容易弄来这点吃的,他又怎能舍得扔下呢。 二白靠吃狼肉过活,又朝东北走了半月多。这天中午他走得累了,也把狼肉吃完了,在歇脚时朝前边用手搭凉棚一望,隐隐约约地看到在远处有座山,他又用心地仔细看,依稀可辨,那山是一大一小。二白心里头一阵惊喜:莫非那就是苏武泡子东边的大小红山吗?店家不是那么说过么?想到这里,二白叨念起来:“小月呀小月,你到底在哪里呀?你要真是住在苏武泡子,前边的山真是苏武泡子旁边的大小红山,我可就找到你了!” 想到这里,二白也顾不上歇了,抬腿急急地朝前奔去。不料刚刚走出了七八里路,忽然从一旁的树丛中窜出一条金钱豹来。这只金钱豹呼呼地叫着,只几眨眼的工夫,就蹿到他跟前来了。豹子大张着血盆样的大嘴,直朝二白奔来。 二白两眼一闭,心里说:“小月!我没有死在狼嘴里,却倒要死在豹子嘴里了。我不能在阳间见到你,那就等到了阴曹地府再相见吧。” 二白默默说着,一等,两等,也等不来金钱豹吃自已,怎么回事呢?他忽然听到金钱豹在呼哧呼哧地喘起粗气来了。二白觉得奇怪,睁开眼一看,呀!原来是来了一大群树蜂,在金钱豹头上蜇着,那豹子被树蜂们蜇得鼻青脸肿,连眼都睁不开了。 二白又像前回打狼那样一下子来了力气,他一蹿骑到金钱豹身上,又是抡起拳头猛打起来。没料到这豹子骨架硬,身子又大又壮,它被二白打得疼了,“嗷”她叫了一声,驮着二白跑起来。这时二白骑在金钱豹身上,他怕被豹子甩下来摔坏了,也不敢再打它了,双手紧紧抓着豹子的毛皮,一任它拼命跑去。 豹子跑了几里路便想停下来,看来它是跑累了。二白才不干呢,他用两腿一夹金钱豹的两肋,那豹子又受疼又受惊吓,只得又拼死地飞跑。豹子被树蜂蜇肿了两眼,看不准方向,二白坐在豹子身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豹子是一直朝东北方向的红山奔的, 他想:“就让这豹子当我的坐骑,把我驮到红山去吧,也省得我用双脚赶路了。” 还真是,等金钱豹驮着二白刚刚跑到红山脚下,累得它连口气都没有来得及喘,就趴在地上死了。 二白先登上大红山找了个安身的山洞,这山洞是白大将军征北时住过的,里面放着点剩下的蜡烛和刀、斧等物,还有钻木取火种的钻。二白可高兴了,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安身的好地方,既可遮风避雨,又可防狼虫虎豹,住在这里寻找小月,又安全,又方便,真是再好不过了。 二白把死豹子扛进山洞里,就下山直奔西边的泡子去了。这泡子好大呀,看上去,足有两三顷地大小,泡子里的水清得有些发绿。泡子旁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刻“苏武淖尔”四个大字,淖尔就是俗语说的泡子。不到苏武泡子,二白想这苏武泡子;到了苏武泡子,二白又觉得陌生迷惑:“小月说家住在这苏武泡子,可又到哪儿找她的家呀?” 苏武泡子的水面平静得如同一面大镜子,除了水边上过冬的芦苇和枯干了的菖蒲,连只水鸟也看不到,更不用说找个有人烟的地方了。二白围着苏武泡子转了一遭儿又一遭儿,什么也找不到,他只好回到了大红山上的山洞里去。 二白先是把死豹子剥了,接着又拿起钻来钻木取火,点上了蜡烛,他用捡拾来的柴草烤起豹子肉来吃,吃饱了,就去苏武泡子上喝水解渴。 入夜了,月光下的苏武泡子更是宁静得很,天无声,地无声,除了水里偶然间有鱼跳的响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了。二白听人说过,狐仙好在夜间行动,行动时还会有小红灯笼出现,他决心眼睁睁地转悠一整夜,看看小月和她家的人出来不出来。 也不管二白如何思念,一天天过去了,从春天的百草生芽,万卉吐绿,到夏天的繁花似锦,蝶舞蜂飞,半年过去了,二白日日在苏武泡子上转悠,夜夜在大红山上搜寻,始终不见小月的踪影,这苏武泡子和大红山上印满了二白的脚印,泡子边上被二白踏出了一圈小路,大红山上的石头也被二白的鞋子磨光了。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大雪飘,又是一年春雷震,又是一年北风号。 日子过得比穿梭还要快,又是三年过去了。这三年,是二白像野人一样住山洞过三年,是他像牛羊那样吃草籽和野果活过来的三年!三年来,二白没有吃过米面油盐酱醋,忘了酸辣香甜咸淡!这三年比河神庙那三年更苦更涩更心酸!他的头发胡子长得老长老长,破衣烂衫比那街里跑着的疯子还要怕人,还要难看。 三年来,二白穿破了多少双自己打的草鞋说不清,反正大红山上的树木,全被二白打柴打去烧了。这天没得烧了,二白只好又到小红山上去打柴。小红山很小,山上长得树木也很少,只有山顶上那一棵碗口粗的枯木,早已没了树帽,是棵半裁子树。二白抡起斧子,乒乓乒乓地砍起来。 树朽干不烂。二白正砍得上劲儿,忽然听到身后有人问话,那声音瓮声瓮气地:“是谁在我家屋顶上闹动静呀,把我老头子的好觉也给扰了!” 二白站起来回身一看,也不知从何处来的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一根龙头拐杖,正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二白说:“我没的烧了,来这儿打柴,没料到惊扰了您老人家,真对不起。” 白胡子老头说:“你是哪儿来的人呀?怎么从来也没见过你呀?” 二白不会撒谎,便把自己的事全对白胡子老头说了,怎么来,怎么去,从头到尾,一五一十,把要找小月的打算全讲了。 白胡子老头听二白说完,就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既然人家同你断了缘分,小月又怎么会跟你见面?她更不会同你一起回去。好了,劝你及早死了那份心,快快回你那老家去吧。” “见不到小月,我就是老死在这里也不回家去!” 白胡子老头说;“你这个人还真够得上四个字,痴心梦想!要是小月能来见你,能让你在这儿等这三年吗?”说完,白胡子老头手挂龙头拐杖,一步步走下小红山去,一眨眼,就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二白可犯起了疑惑,按着白胡子老头刚才走过的地方去查看,点点儿的狼痕迹地找不到,真够奇怪的了!二白想,我来这里三年多了,也从没见过这老头出来过,说不定这就是小月家的人,也是狐仙变的。他说我在他家屋顶上闲动静,他的家既在下面,我就去找他家的门口,没门没口,他又怎么出出进进呢?” 二白跳下小红山来,左找右找,上看下看,前走后走,察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把个小红山搜寻遍了,不用说找不到白胡子老头的家门,就是连个巴掌样的口口,鸡蛋大的洞洞窟窿也找不见!二白丧气了,柴也不打了,没精打采地走回大红山的山洞里去。 人老岁月不老,春回大地,苏武泡子里冰封化开了,树木泛绿,大草地上又开满了各种鲜花,大雁飞回来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清晨,二白正在做梦,就听到苏武泡子那边有个孩子的嬉闹笑声。这地方又哪来的小孩子呢?二白忙跑过去看。只见那小孩子坐在一个大蒲墩上,这个大蒲墩放在水面上,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根水草,在拍打着身下的水玩耍取乐。二白简直看得呆了,这小孩子是个男孩,生得又白又胖,穿着一个红兜肚,头上梳着用红线绳梳的一支“通天蜡”,非常惹人喜爱。 二白不错眼珠地看着水面上的小男孩,小男孩也发现了泡子岸边的二白,他用手一按一拔地划着水,坐着的大蒲墩像只小船一样直朝二白站立着的地方冲来。 快到跟前了,小男孩忽然问道:“喂,你是从单家庄来的人吧?” 二白忙说:“是啊。” 小孩子又问:“你在路上吃了一只老狼?” “是呵。你怎么知道?” “听我娘说的。你还让豹子驮你到这儿,把豹子也吃了?” “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娘告诉我的。喂,你是不是姓单呀?” “是姓单。” “叫不叫二自?” “对,是叫二白。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也是俺娘告诉我的。” “你娘告诉你这些干什么?” “好认爹呗,认错了哪行呀!” 二白心里一半来一半忧,紧接话头又盘问:“你娘是谁呀?快说给我!” 小孩子说:“俺娘是俺娘!” “你娘她叫什么名字呀?” “不知道!” “谁是你爹呀?” “你呗!你是俺爹!” 二白明白了,这是小月给他生养的儿子呀!小孩子同二白一问一答,一答一问,说话间,小孩子坐着的大蒲墩靠边了,二白忙弯下腰去把小男孩抱起来,他亲亲他的脸蛋儿,小孩也不惧怕他那模样,反而亲热地用两只小手抱住二白的脖子。 二白问儿子:“你叫什么呀?” “还没名字呢,俺娘说要让爹来起名儿。” 二白又问儿子:“你娘怎么不来呀?” 儿子说:“俺娘说了,她不愿见到你,不来了。让咱俩回老家去。” 二白很伤心,虽说有了三岁多的儿子,可是不能再和心爱的妻子见上一面,他越发悔恨当初自己做错了事!他问儿子:“你娘她住在哪儿呢?” “不知道。” “你姥娘家住在哪儿呢?” “不知道。” “你从哪儿到得这儿呢?”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二白没法子了,看来只得同儿子一同返回老家了,总不能让儿子也过这野人一般的生活呀!可是,要回老家,这又有多么难呀,身上又没有长翅膀,这么遥远的路程,又该如何往回走呀?二白又后悔当初不该把自己那匹马放走,有那马,回归老家要方便多了。 正当二白这样想的时候,耳朵里猛然间听到咴咴咴一阵马叫。他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匹马迎面跑来,马越跑越近,越近越眼熟,哎呀,这不是三年前自己放走的那匹马吗?那马也见到了旧主人,扬着头,又咴咴地嘶叫了起来。 二白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下,抱着儿子骑上马,追星赶月般地循着来时的路线返回去了。 这一日终于赶回单家庄来了。父子俩骑着马前脚刚进村,后脚天气就变阴了,只听得雷声隆隆,大雨从天上哗哗地泼了下来。二白同儿子先来到哥哥家。二白一进院门,穷大秀才还以为是个流浪汉来他家避雨, 就问:“你找谁呀?” 二白说:“我是二白呀。哥哥,连我也不认得了?” “什么?你是二白?”穷大秀才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二白跟前,周身上下地打量着:“弟弟,你一去就是三年,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你又吃大苦、受大罪了呀!” 二白对哥哥说:“哥哥,吃了苦,受了罪,打心眼里觉得倒踏实。”说到这儿,他抱过儿子来说:“叫伯伯。” 穷大秀才一见侄儿长得又壮实又机灵,就问:“弟妹呢,怎么不见小月啊?” 二白对哥哥详细地学说了一切,说:“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小月了。" 有了儿子,我一心一意守着儿子过,决不再娶了。我伤害了小月,是我二白对不起她。” 风雨停了,天上又露出了红艳艳的太阳。二白急着要回家去看看,乔氏拿出钥匙,对二白说:“他叔,这是你家房门上的钥匙,我和你哥哥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过了。” 二白从乔氏手里接过钥匙,别了哥嫂一家人,骑马带着儿子回到家门口,呀,大门敞开着,莫非家里着贼偷了吗?二白顾不得多想,急忙跳下马来,刚刚抱着儿子进入院里,就见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二白定睛细看,不由失声地惊叫了起来:“小月!是你呀!” 小月说:“你在大红山三年,你的真心诚意,感动了我的父亲,更感动了我,家父这才格外开恩,准许你我夫妻破镜重圆。家父只提出一个条件,要我挑选:如果同你重做夫妻,就得废去五百年道行;如要道行,就不得团圆。为了我们的情义,为了孩子,更为了不辜负你对我的真诚,我忍痛舍去了修炼五百年得来的道行,回到了咱的家来。刚才那场风雨,就是我废去道行,反叛族里,永为人类的洗礼呀。从今往后,我小月再也没有狐仙的变化功力了,经过脱胎换骨的洗礼,我改变成人世间一员了。” 二白听小月说完,更为妻子的真诚果敢感动了,他盟誓向小月:“我们两口子再也不分离了!” 从此,小月和二白男种田女纺线,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直到白头,再也没有分开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eizhongcaozia.com/hzczxzjb/62229.html
- 上一篇文章: 秋冬靓汤,丰水梨红枣炖排骨,收服全家人的
- 下一篇文章: 草莓,是胃炎的催命符吗消化科主任养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