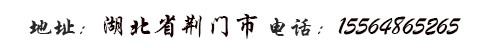思源丨黄纪苏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汉化
|
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汉化 文/黄纪苏 “刘平国”仨字最初在我这儿引起的联想是某位当代援疆干部或工程技术人员,后来阅读刘平国刻石的相关资料,又会想到当代的国际关系如中美东盟五眼联盟之类。没办法,这是门外汉路过史学殿堂时既可怜又正常的反应。历史学家最能对历史上的人、事给予“同情之理解”,希望他们也匀一点儿给我这个在门口东张西望、胡思乱想的汉子。刘平国铭文不长,先抄在这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得)[1]□谷关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 初读这段铭文心头一动:拜城一带在没汽车没公路的近两千年前对于中原当属极西远荒之地,中国味儿竟这么足,龟兹将军居然不姓“库尔班”、不叫“阿依波力”而姓姓遍大江南北的“刘”、叫重名率紧跟“建国”“保国”的“平国”,而且还使用中原王朝的纪年,甚至那两句标语口号都不用怎么改就能直接贴首都机场的高速路边。今天,我就趁着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难得机会,从汉化的角度汇报一下自己在恶补这段历史时生出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困惑。▲ 刘平国刻石清晚期初拓本 吴昌硕、杨岘、张度跋 [1]学者多释读为“从”,但也有释读为“得”的,因与后面的讨论相有关,故在此先做标注。 使用“汉化”这个词我有些犹豫。它并无歧义,就是汉文化的一套被其他文化接受。时间也不是问题,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秦或先秦,“汉奸”“汉化”之类字眼就有点别扭,而刘平国勒石记功发生在后汉而且离关张不远。那为什么还犹豫呢?因为“华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套个汉姆莱特句型:“华”还是“汉”,这是个问题。“华夷之辩”有文化偏至的色彩,但多少还讲点道理,不像“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不管不顾、“我”字当头,被今天的小粉红拿去刺青就更没法看了。“华”的优势在于它上承华夏,下接中华民族,融汇了四夷八荒诸多元素,动态而发展,虽然还是圈子,但这个圈子的时空格局要远大于“汉”。况且今天的汉族相对于其他五十五个兄弟姐妹的绝大多数,除了高考不享受加分,已是徒有虚名了。但“华化”也有个缺点就是过于生僻,陈援庵先生著有《元西域人华化考》,那是近百年前的事了。“华化”其实就是“中国化”,那为什么不在“中国力”“中国能”“中国道路”“中国故事”如猛火烫油的形势下就用“中国化”呢?那是因为我们在谈历史,历史上的“中国”伸缩不定,跟现在的版图颇有出入。我们在古今之间往来游走,万一走丢一块国土,政治上出问题,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为稳妥起见,还是用了“汉化”。▲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励耘书屋刻本,年,28.3×17.8cm 当年西域的汉化有它的背景,国际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当年的国际关系,汉匈对峙又是重中之重。汉匈一南一北,一农一牧,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扩张冲动,因为农田和牧场一样,有够是暂时的,没够是永久的,耕地多了,草地就少了[2]。更何况对土地的追求,经济、生产方式也只是动因之一。都说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是战斗民族,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又何尝不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七国之乱,六百年间“和”字何曾有过立锥之地?战不战斗并不取决于是两条腿行军还是四个蹄子奔袭。扩张在内是社会矛盾,向外是民族矛盾,二者还会互相转化[3]。秦一了宇内却一不了匈奴[4],只能“却胡”;白登之围,大汉的国父险些做了俘虏。中原王朝的外部敌对势力,匈奴不是唯一却是第一。以汉初的内外形势力量对比,匈啃不动汉,汉也吃不下匈而且显得被动,于是“约为昆弟”,沿长城划势力范围,墙外的“引弓之国”归匈,墙内的“冠带之室”归汉,真跟哥们儿“分家析产”似的。匈奴就在那时候进入西域。但形势会变化,战略也会调整。到武帝时国家由无为转为厉害,遭遇到两千年后“粮食太多吃不了怎么办”的难题,于是开始为弟弟张罗截肢手术:东边迁乌桓断匈奴左臂,西边通月氏联大宛断匈奴右臂。依违在两霸之间的西域诸国十分不易,弄好了一边嫁一公主过来,弄不好两头轮流兴师问罪。▲ 华岩《苏武牧羊图》 汉与匈前后脚来到西域,它们与当地的关系有同有异。匈没把西域当统战对象,而是当了韭菜地[5]。虽说是夏的后裔,匈奴却披发左衽,作风粗放,武力之外好像不依靠也不具备软实力,击月氏,拿国王的头骨做酒杯。刀架在脖子上,西域诸国只好要什么给什么[6],匈奴使者带着单于开的证明信出差西域诸国,所到之处食宿有安排、交通有保证[7]。汉是后来者,离得又远,可能在西域诸国眼中就是人傻钱多的大户[8]。中原最看重接待规格、首长通道这些事情,而汉使却“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跟高速公路上排队缴费、差一毛钱也甭想过去的普通司机一样,其憋屈可以想见。直到汉兴师动众破姑师、征大宛,才算扭转局面。▲ 贵霜迦腻色伽铜币 公元2世纪,直径2.5cm 与匈奴相比,汉朝的核心竞争力确实多元一些,有“兵威”有“财贿”还有“汉家仪”,大概折合今天的“富起来”“强起来”以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个后面会再谈。不过汉朝经营西域,并不是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吃拿索要并不手软,杀也是常事[9]。汉军在西域东征西讨,相关国家不但要箪食壶浆做好后勤,还得送郎参军,人数往往是汉兵的很多倍[10]。相对于汉,西域都是绝对小国,于阗“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鄯善“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渠勒“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11];精绝小到国王直接审判日常民事纠纷,连内地的县太爷都到不了,也就相当于村支书吧。人力、物力上的摊派肯定是不轻的负担,与匈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相比哪个更沉重,就得请教各位专家了。▲ 《汉书评林之西域传》 班固撰,凌稚隆辑评 明万历十一年吴兴凌氏刊本 (左右滑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eizhongcaozia.com/hzczzzys/61346.html
- 上一篇文章: 4种水果或有助孩子长高个提醒平时常给孩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